【散文】念父② ‖ 曾焱

念父

曾 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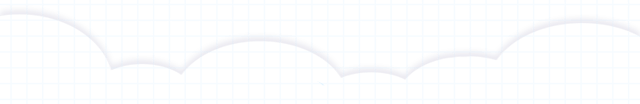

四
父亲于1969年退役,此时部队已从丹东调至乐山。回乡后,经侄女曾润光介绍,结识我母亲。母亲的家,在赤水河镇斜口村富家坪,也是穷苦人家。
母亲时年26岁,在农村已属大龄女。但那个年代,却是村中罕有的初中生,识见自是不同。旁人介绍的相亲对象,她一概不满意,一直苦等高山流水旁走过的白马少年,以致人生大事延宕数载。然,母亲坚定不移,深信必有良缘俟于将来。最终,等来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父亲。母亲与父亲很快迈入婚姻殿堂,过上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日子。我常感慨父母的结合——人生,真有一种缘分,不远不近地等着你。

听父亲讲,他参加工作不久,某日散步时路过一民房,惊闻一阵呼救声传来。军人的警觉使他踹门入内,循声而去,竟窥见茅厕中几近淹没的呼救者。他不加思索跳将下去,在粪水里托起一位妙龄女子。费尽千辛万苦,方把花容失色的女子推至安全处。他朝其身上冲两桶水,也往自己身上胡乱冲冲,即抽身而去。很久,女子父母方打听到英勇的父亲。感恩戴德的一家人专程到厂里,向父亲致以深深谢意。
彼时,领导们方知其英雄之举。因父亲在单位一贯有上佳表现,领导们当着这家人之面,又猛夸父亲一阵。后来,女子父母委婉表达,想把女儿的终身托付给父亲。父亲急摇手,申明早已婚配。是啊,在父亲眼里,母亲才是永远的“佳人”。
记忆中,二老也要吵嘴,父亲大多时总是让着母亲。某次,父亲和母亲斗气后,两天互不理睬,但私下却悄悄对我说,“别看我同你妈吵嘴,我们家还真少不得她呢!”多年来,好强的母亲也因父亲之脾气而深感欣慰。父亲走了,我们一家都很不习惯。
其实,最不习惯的,当属母亲。父亲的呵护,早已深入母亲骨髓,填满母亲灵魂。听女儿讲,葬完父亲,母亲悲哀欲绝,趁我们上班后即闭门痛哭,一时哭得椎心泣血,哭得肝肠寸断,哭得天地失色。古稀之年的母亲仰天悲呼:“天,天啊,咋让我成了寡妇?”
两个多小时的哭泣,母亲方把沉积半生的泪水流完。毕竟,母亲与父亲温温相守的四十九年中,除我二弟早夭之外,再未流过悲伤之泪。俗语云:“老伴老伴,老来相伴。”父亲的生命甫一塌方,母亲顿感成了孤独无依的断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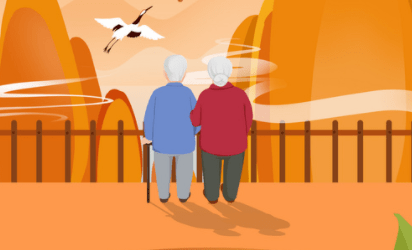
五
父亲退役翌年,通过招工进入古蔺岔角滩铁厂,成为一名人人羡慕的工人。那个年代,工人头顶都有层耀眼光环,素有“工人老大哥”之说。后来,又先后调至煌家沟铁厂、青龙嘴煤厂、青龙嘴酒厂。
身处任何单位,父亲均视勤劳为立身之本,视尽责为立业之基,常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父亲过世后,我们整理其遗物,发现一枚“先进工作者奖章”,系古蔺县委县人民政府颁发,颇有分量。一般而言,需连续几年当选厂里先进,方能为县上先进。各种荣誉中,最具特别意义的,当属青龙嘴煤厂发的一本荣誉证书,其落款日期为1996年。这一年,不正是父亲下岗那年吗?足见,勤劳的父亲见单位濒临倒闭,依然毫无怨言,不改军人本色,坚持站好了最后一班岗。
也难怪,父亲在青龙嘴煤厂上班时,郎酒厂一领导想调其任保管。这位领导曾与父亲共事,极重父亲克己奉公、忠于职守之品。父亲曾在青龙嘴酒厂从事保管工作,从未出任何差错。只是,素不求人的父亲未去打点关系,终未进入名企之门。否则,其命运必随郎酒的跨越而改写。父亲唯一一次求人,是为我办户口之事。我考上泸州师范学校后,母亲担心户籍管理者吃拿卡要,遂买两瓶古蔺大曲——彼时的“重礼”,叫父亲提上,送给办理者。未料,素来忠厚的父亲待手续办妥后,方从提包里掏出酒瓶。他羞于办事前送礼,却乐于事成后感恩。看得出,某些事于他而言,确非能与不能,而是愿与不愿。母亲为此后怕不已,认为差点误了大事。后来,耿介的父亲待我至泸师,即选择艰辛的井下工作。每日推着矿车,走向几千米深处的隧道,在最危险之地挥汗如雨、挥稿挖煤——那是最高劳动强度的工种之一。

某年暑假,我回到家中,曾在矿井守候父亲回家吃饭。当运煤矿车哐当哐当地从黑森森的矿井里爬出来时,车后都有一位满面漆黑的工人,惟张嘴时牙齿方露出一点白。是时,我竟不识谁是父亲……
上世纪80年代末,企业对安全生产重视程度远不及今日,即便是国有煤矿,每年皆有工人丧身井下。父亲讲,生命在井下,比什么都脆弱,任何安全帽均抵不住岩石之坚硬。他说,有一镜头永远定格在记忆深处——某次,井下塌方,救援工人施救许久方出来。然而,手里仅提着一条血淋淋的腿。彼时,围观者无不战战兢兢、毛发悚然,几欲先走。
如此惊恐场面,并未吓到父亲。他整日在井下同黑暗抗争,与死神共舞,只为满足我在校之花费。毕竟,井下工收入比地面工高。记忆深处,父亲吸烟颇“凶”,食指处从来焦黄一片。但某年寒假回家,竟见他不再吸烟,只是不停地喝着粗茶。显然,他能戒掉近二十年的烟瘾,都是为了保证我日渐增长的开支啊。回想泸师那段岁月,确有愧对父亲之感——与多数同学相比,我兜里常有零碎闪银,不时可到小馆酌两杯;平日衣着时髦,街上流行的西装、运动服、T恤皆很快装扮在身。然,学业并未随年岁增长而日益精进,甚至出现挂科现象。
父亲一生最自豪的事,是当选为县人大代表。据传,组织上本有人选,但工人们偏要选父亲。厂里工人多来自农村,善良质朴,重情重义。当然,骨子里也不乏执拗。他们称,既是人民代表,辄须代表广大职工的利益,敢建诤言,敢说真话,不趋炎附势,不随风而倒。而这些特质,均是铁骨铮铮的父亲身上所有。他一生表里澄澈,生性率直,不筑城府,不看风色,不搞投机,尤喜仗义执言。于是,工人们略略商议后,即举起神圣选票向父亲走去。
后闻母亲讲,凡在企业当选的县人大代表,多有晋升副厂长者。但是,副厂长由县计经委任命。凛然卓立的父亲却不愿低下头颅,去谋求一官半职。此般特质之养成,与其早年成长环境、部队熔炉锻造所关甚巨。父亲幼时,在目不识丁却能诵《三字经》的奶奶熏陶下,即知“德”之要义,素来睥睨吮痈舐痔、溜须拍马之徒,怎会去讨好所谓要人呢。他在那些趾高气扬的领导面前,从无谄媚之容,亦无趋承之态,一生未能在单位混得有模有样,确为性格使然。受父亲性格影响之故,我在工作和处世上懂得尊重,却不懂顺从;懂得踏踏实实,却不懂忍辱负重,导致得罪不少领导和朋友。
六
父亲一生呆过的企业均不景气,所得薪水仅能维持家中日常开支。有时,单位推迟发工资,甚至因发不起工资辄三两月放假。但是,父亲从不允许别人瞧不起其单位。倘有人嘲笑挖煤工人,父亲常义正言辞驳斥:“挖煤工人咋了?咱一不偷二不抢,一样凭本事吃饭,从来不坑国家不坑党,低谁一等吗?”
有时,遇上家中境况窘迫,母亲辄忍不住发发牢骚,调侃一下父亲单位。每每此时,性情平和的父亲极生气,常大声争辩:“我端的是‘铁饭碗’,再差也不至于没饭吃,你看共产党何时放弃自己的企业?”
是啊,父亲本苦难中挺过来的人,其幼年到青年历经坎坷,备受屈辱,好不容易在部队找回尊严。几年戎装生涯,已将“家国情怀”融入血液中,已将“忠信笃敬”根植信念里。他对党国之爱,对单位之爱,至死不渝。他深信,党和政府不可能对企业死活置之不顾,不可能对工人生存置之不顾。终有一天,青龙嘴煤厂会越来越好,我们一家会越来越好。
行笔至此,忽忆起那句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没错,父亲不懂诗歌,却拥有诗人的情怀。
七
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洪流中,“下岗之潮”很快席卷全国。父亲自不能置身事外,于1996年成为一名下岗工人。
下岗,对父亲打击很大。彼时,我在护家中学任教,母亲帮我们带孩子,他失魂落魄地到护家时,脸上写满了苍老。那双曾经透出光芒的眼睛,竟皱纹横生,低垂无神,疲惫迷茫。他整日埋着头,不停地唉声叹气,仿佛世间之苦均聚在一起,如奔矢般扎向其心头。我们不知如何安慰他,一家人均难接受这个现实,感觉被整个世界抛弃一般。那段时日,家里充斥无边的失落、悲凉、伤感。而他,更是彻夜忧愁、痛苦、失眠。我们确未料到,从部队到企业堪为标兵的父亲,一夜之间竟穷途末路、气短苍凉。
所幸,我和妹妹均已成家。妹妹住在双沙,孩子郭毛需要人带,父亲遂过去照顾外孙。自此,妹妹无论迁往古蔺还是成都,父亲一直跟随他们。郭毛升入初中后,父亲方回我们身边。
下岗对父亲打击虽大,但他并未因此而牢骚满怀。短暂的剧痛之后,他一直保持平和之心性,达观之胸怀。那些远没他善良,也远没他正派的厂领导下岗后,或开煤矿,或搞货运,或建码头,过得风生水起时,他也不羡慕,更无絮絮闲言,从不质疑其资金来路。或者,按母亲之说——父亲就一老实人。
终其一生,阅尽人间百态,身藏半世离恨,怀揣一生心酸。但是,尽管屡陷困境,却从无愤世嫉俗之悲愤,亦从无呼天抢地之哀怨。在其眼里——痛,实为命运;苦,方为人生。
父亲在妹妹家里“上岗”后,竟很快恢复笑脸。为照顾好妹妹一家,特买来菜谱,研烹饪之诀,调生活之味,将平淡日子抹上丝丝缕缕的温情。后来,父亲回泸州后,我特爱吃他做的红烧牛肉,我爱人则认为其蘸水做得最好。有几次,表妹带孩子来玩,专点父亲做的土豆炒回锅肉。对此,他十分自豪,择菜淘米时总忍不住哼起红歌。看得出,父亲是不向命运低头之人。尽管每天忙的都是柴米油盐,他也要在细微末节上体现自身价值。年轻时,他挑起一家人的重担;年老了,也拒绝成为家庭负担。
尽管,他就一普通百姓,给不了我们权势,给不了我们虚荣,也给不了我们金钱,但却给予我们最生动、最直观的做人示范。这,不正是平凡之家最宝贵的财富吗?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曾焱,1972年8月生于四川叙永。曾先后在古蔺县兴阳小学、护家小学、护家中学、古蔺县委办公室、古蔺县二郎镇、泸州市委办公室、泸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2016年9月任中共古蔺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2020年3月任中共古蔺县委副书记。2021年6月任泸州市科学技术和人才工作局党组书记。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曾 焱
配图:方志四川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