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基于比较视野下日籍《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的价值与特色‖万良华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1期
基于比较视野下日籍
《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的价值与特色
万良华
《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书影
1898年,日本东亚会和同文会在东京合并,以“保全中国”为口号,成立东亚同文会。1900年,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书院,培养经略中国的人才。该书院组织学生先后对中国进行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实地考察,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调查面之广,为全世界所罕见。参加考察者多达5000余人,考察路线700余条,“调查面包括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民族关系、文化教育、社会风俗、交通地理,甚至边疆关防,在此以前,尚无哪一届中国政府,能够做到此点”。
东亚同文会以书院学生的考察报告、调查日志为基础,参考相关资料,先后于1915—1921年、1942—1946年编纂成《中国省别全志》(18卷)、《新修中国省别全志》(9卷),其目的在于了解中国、研究中国,为侵略和占领中国服务。其中,《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简称四川卷)、《新修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简称新四川卷)是该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对四川省志有有益补充,也是后人研究抗战前四川社会的重要史料;且东亚同文书院踏察调查之初的组织架构、民间组织的调用,日本学者编辑中国地方志书的特色,既内容缜密又极具功利性,其经验和问题等,都值得我们研究,并加以思考和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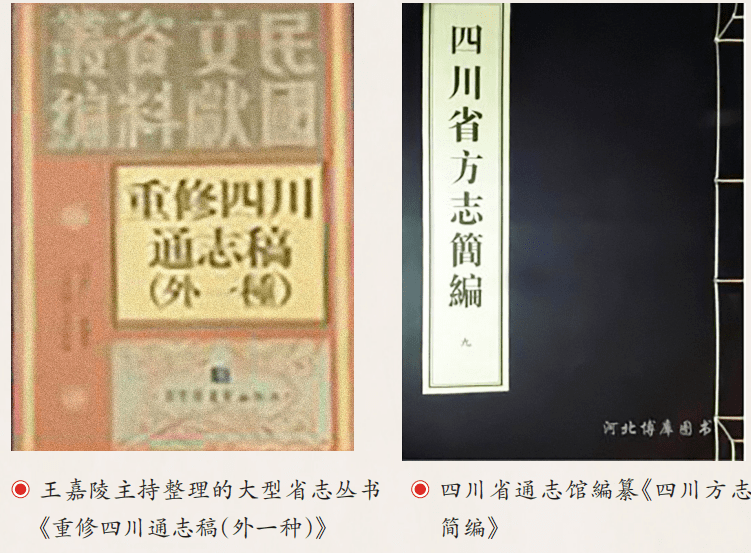
一、四川卷的重要价值
(一)比较视野下百余年四川省志纂修
明清以降,四川修志传统繁盛、绵延不绝,且体例日趋完备,内容丰富,记载详实,数百年间川内各府、州、厅县纂修地方志书达600余种之多。四川省现存明清两代纂修的四川通(总)志共7部,上自明正德十三年(1518),下迄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分别为明正德十三年(1518)《四川志》和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明万历九年(1581)、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清康熙十二年(1673)《四川总志》以及清雍正十一年(1733)、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四川通志》。“巴蜀之典章制度、文化之要籍,连绵不绝,于志可徵,向为世人所称道。”②然自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至1949年,132年时间里,四川省志的纂修陷入窘境,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四川省志纂修数量较此前出现断崖式下跌。这个时期,国内编纂的四川省志仅两部:宋育仁总纂修的《重修四川通志稿》、陶元甘主撰的《四川省方志简编》,其余两部则为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四川卷和新四川卷。
二是与此前相比,国内纂修的四川省志内容完成度、丰富度不够。《重修四川通志稿》内容丰富,但因总纂修宋育仁于1931年去世,未完全定稿。“现存《重修四川通志稿》,因各志出自众手,受各种因素影响,进度也不一致,其中一部分如建置志、舆地志、官政志、食货志、礼俗志、学校志等基本形成初稿,而另一部分如人物志和民职志,则只是把资料搜集起来,甚至还没有很好地整理和编排,更接近于草就的资料汇编。一直到民国20年(1931)12月宋育仁病故,《重修四川通志稿》都处于一半初稿、一半资料长编的状态,虽林林总总300余册,离统稿杀青却还有距离。”《四川省方志简编》完成度高,但内容丰富度不够。王嘉陵在《重修四川通志稿(外一种)》的前言中说:“《四川省方志简编》……条理清晰,行文简洁生动,却又不失志书所需之规范,只是体量规模远逊于《重修四川通志》。”2015年9月,由王嘉陵主持整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重修四川通志稿(外一种)》58册,《四川省方志简编》仅占第59—62册共4册,也可窥见其体量。
三是国内纂修的两部四川省志均为稿本,未刊行,因此流转度、利用率极低。《重修四川通志稿》《四川省方志简编》填补了清嘉庆之后至民国前期(部分使用资料已达1929年)百余年间无省志的空白,且编纂于帝制结束、共和肇始时代,加入若干社会因革变迁、新生事物等内容,为近代四川历史研究保留了较为重要的文献资料。遗憾的是,民国时期国内纂修的仅有两本四川省志均未刊行。《重修四川通志稿》自编纂之日起,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已经逼近,及至成稿,侵华战争不断扩大,举国上下,哀鸿遍野,经费紧缺,稿本也辗转流离,竟尘封80余年,渐成残稿;特别是“艺文志”部分,卷帙浩繁,记载详实,却全部不知所踪。1944年《四川省方志简编》“成于四方烽火之际”,誊正后也未能付印,稿本藏于四川省图书馆,流转使用率极低。
(二)四川卷是四川省志的有益补充
一是有效弥补特殊历史时期四川省志记载的缺失。东亚同文会1917年出版的四川卷主要根据1908年第6期“长江班”至1916年第14期“湖北四川班”调查报告和旅行日志的内容及相关材料编写而成;1942年出版的新四川卷主要根据1917年第15期“贵州四川广西班”至1930年第27期班调查报告和旅行日志等内容编写而成。这两本书记录了1908—1930年的四川,其时间节点正好处在保路运动前夕、四川军阀混战及走向统一时期,有效弥补四川这段特殊历史时期资料记载的不足。
二是编纂资料来源及取舍,各有侧重。《重修四川通志稿》在资料来源及取舍上,较前人纂修省志多有创新。更因宋育仁本人为维新派,主张“中体西用、变法维新、改良强国”,且有出使欧洲考察的经历,故在纂修四川通志的材料选择上更多元,除参考旧志外,还多参看政府文件、报告、统计资料及时人著作;又因其一度回川督办商业和矿业,故比较注重对经济史料、国计民生资料、社会变迁资料的收录。《四川省方志简编》取材严谨详尽,注重经世致用,同时还记录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川籍将领,如刘湘、李家珏、饶国华、王铭章、许国璋等。四川卷和新四川卷在总论及概述中对四川沿革等部分虽亦参考中国旧志材料,但数量极少,主要来源还是以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前后多达17次的调查报告和调查日志为基础纂修而成。由于参与考察的书院学生经过严格的有针对性的业务技能培训,其专业能力强、素养较高,同时受西方实证主义影响较深,考察、记录严谨,当时人记录当时事,可信度高;同时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对下层社会生活也有较深入的考察和记录。
三是视角和内容互为补充、验证。《重修四川通志稿》卷帙浩繁,在民国时期四川的4部省志中,体量最大,全书分为建置、舆地、官政、食货、礼俗、学校、艺文、人物诸门,成稿300余册,虽有散逸(除艺文整体丢失外),但总体还算完整。《四川省方志简编》“以简编体兼因革,材包新旧,于致用一端,尤为注意,即就文化人物而论,上已溯夫往古,下亦述及今兹,新政故典,尽聚一编。自对倭作战后,殉职蜀将,罔不记录,冀成信史,以垂来叶”。四川卷和新四川卷则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对四川的记载资料较为可靠,极其详尽,且大量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如拍照,运用近代科学测量技术绘制地图和城镇布局图、测量江河流量和流速等。同时,视角以日本为中心,“常把中国内容与日本情况相对比,同时又因是为扩大在华利益服务……《全志》的志义与中国人编纂中国地志大相径庭”。运用“他者”视角观察和记录当时四川情况,“以外国人的视角看中国,自然不同于国人看自己”,特别是其记录的大量关于民国时期四川的经济情况,可与当时国内编纂的两部四川省志互为补充、相互验证,为研究和还原这段巨变时期四川历史提供更为丰富的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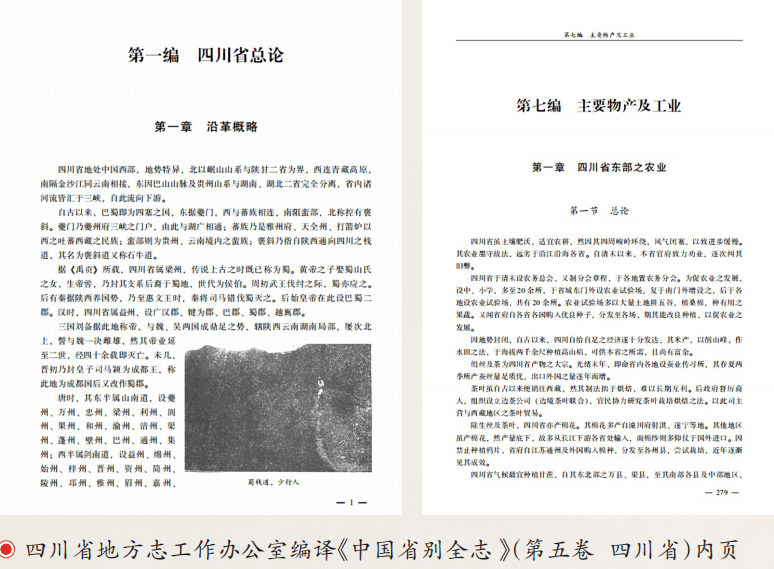
二、四川卷的突出特色
通过与中国大致同时期编纂的四川省志比较发现,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四川卷在框架设定、谋篇布局、材料取舍、内容侧重等方面,存在显著特色。
(一)重现状而忽视传承,缺乏对四川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历史地位的了解和评估
中国地方志的编修历来把“详今略古”和“贯通古今”相统一。“编纂的地方志,在记述的分量上有详略之分,但要以贯通古今为前提,决不能把历史的客观进程删略……通过准确、翔实、系统的资料,记述这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④四川卷虽在第一编“四川省总论”中对四川地理、沿革、行政区划、面积及人口、气候、与外国的关系等有概要梳理,但对四川在古代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到位。“四川因其地形独立,与外省难以形成紧密之联系,是故屡有叛乱者割据于此。如王莽末年有公孙述割据于此;三国时,蜀据有此地;晋时,李特据有此地;唐末,王建据有此地;近代以来,有革命家谋以四川、云南为根据地,其亦是仿效先人之智举。然据四川养其势进而谋中原之尝试,自蜀汉刘备起并无1人成功。此也只可归结于此地实乃偏僻。”实际上,作为四川盆地的中心——成都平原,尽管从中观地理位置看,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的确致使成都通往盆地外部的交通十分不便,但“如果把成都放在中国与亚洲的宏观地理中考察,成都地处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运输线三大交通商贸网络体系的交汇点……看似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反而成就了成都作为中国古代三大交通走廊和经济带交汇点的区位优势”。四川在历代统一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至南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东移南迁,战略防御东北移,四川的地位才逐渐下降。然而,“四川自明清至今,首领西南,兼及西北的重要地位,依然存在。”
(二)内容集中于物产、财贸、金融与交通,缺乏风俗、文教、人物等记载
全书分为10编,除第一编“四川省总论”外,其余9编中,第二编“通商口岸”、第三编“四川省之贸易”主要集中记录通商港口、贸易情况;第四编“都市”主要集中反映主要城市、县城位置、人口等基本情况;第五编“交通及运输工具”和第六编“邮政及电信”集中记载交通和通信;第七编“主要物产及工业”、第八编“商业机构及商业习惯”、第九编“货币及金融机构”、第十编“度量衡”主要记载物产、金融和商业机构等情况。从其谋篇布局和实际内容记载来看,全书所有内容都紧紧围绕经济调查服务于军事、政治目的,对中国传统地方志非常看重的风俗、文教、人物记载少之又少。尽管日本在密谋侵略和占领中国之初,就有人提出“文化亡国”策略,但显然在前期执行过程中,更注重对经济贸易和物产、矿产的调查,这与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开始逐步兴起的近代化、工业化实用主义理念相关,也与日本侵华策略密切相关。当然,书院中后期大旅行调查的内容和方法也在改革,如书院第5期学生马场锹太郎从1916年开始在书院担任教授指导学生大旅行调研后,在21期(1923年)、22期(1925年)学生的大旅行志序文中指出:“为了研究支那,要知道支那的风俗、习惯、物情、民意,要理解人心。”
(三)在产业记载中,更侧重对手工业、工矿业的记载,对农、林、畜牧业记载较略
第七编“主要物产及工业”中,记载手工业、矿业、工业达113页之多,其中对生丝、绢织物、棉花、棉布、麻、棕丝、砂糖、药材、大黄、麝香、姜黄、五倍子、木耳、白蜡、黄蜡、桐油、木油、山羊皮、绵羊毛、牛皮、猪毛、牛脂、盐、铁矿、石炭、铜矿、硫磺、金银矿,以及重庆、成都的工业生产和运输方式、市价、征税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对四川农、林、畜牧业记载的篇幅总共23页左右,主要记载“气候土壤”“水利”“农业组织”“耕作方法”“农具、用具”“收获、总收益”等,缺乏对粮食作物产量和潜力的详细调查,更多局限于耕作方式等的考察;而实际上,粮食作物的生产能力是支撑农业社会的重心,对于农业大省四川来说,其调查和记载有失偏颇。
(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1期 )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万良华(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配图:方志四川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