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三星堆】陈立基:半生书写千古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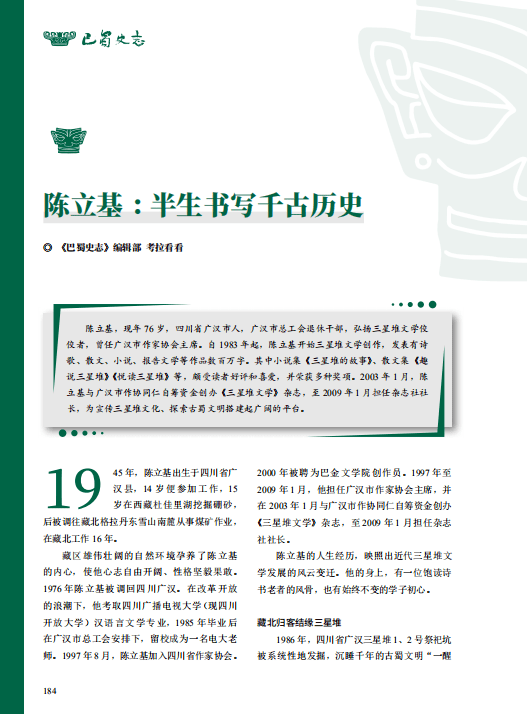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陈立基:半生书写千古历史
《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
陈立基,现年76岁,四川省广汉市人,广汉市总工会退休干部,弘扬三星堆文学佼佼者,曾任广汉市作家协会主席。自1983年起,陈立基开始三星堆文学创作,发表有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数百万字。其中小说集《三星堆的故事》、散文集《趣说三星堆》《悦读三星堆》等,颇受读者好评和喜爱,并荣获多种奖项。2003年1月,陈立基与广汉市作协同仁自筹资金创办《三星堆文学》杂志,至2009年1月担任杂志社社长,为宣传三星堆文化、探索古蜀文明搭建起广阔的平台。
1945年,陈立基出生于四川省广汉县,14岁便参加工作,15岁在西藏杜佳里湖挖掘硼砂,后被调往藏北格拉丹东雪山南麓从事煤矿作业,在藏北工作16年。
藏区雄伟壮阔的自然环境孕养了陈立基的内心,使他心志自由开阔、性格坚毅果敢。1976年陈立基被调回四川广汉。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他考取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现四川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毕业后在广汉市总工会安排下,留校成为一名电大老师。1997年8月,陈立基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2000年被聘为巴金文学院创作员。1997年至2009年1月,他担任广汉市作家协会主席,并在2003年1月与广汉市作协同仁自筹资金创办《三星堆文学》杂志,至2009年1月担任杂志社社长。
陈立基的人生经历,映照出近代三星堆文学发展的风云变迁。他的身上,有一位饱读诗书老者的风骨,也有始终不变的学子初心。

2006年12月5日,陈立基(左三)陪席慕蓉(左四)参观三星堆(陈立基 供图)
藏北归客结缘三星堆
1986年,四川省广汉三星堆1、2号祭祀坑被系统性地发掘,沉睡千年的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坑室出土的青铜、玉器、石器等数以千计。当即,这一神秘奇谲的历史遗迹引得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广汉一时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当时,陈立基正在为留校电大做准备,培训班的老师叮嘱他要万分留意三星堆考古进展。陈立基牢记老师的话,一直关注着三星堆遗址发掘进展。随着三星堆遗址发掘进程不断推进,纵目面具、青铜神树、青铜兽面、太阳形器等独特的器物文化渐渐被披露。陈立基对这些文化瑰宝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主动探寻隐藏在这些玉石、青铜背后的历史和故事。
在资料寻找过程中,陈立基遇到一些问题。三星堆出土文物不同于其他地区出土文物,其他地区出土器物特征往往有迹可循,但在三星堆遗址发掘过程中,无论出土多么精美的青铜玉器,都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记载。当时外界对三星堆遗址的解读资料也非常少,苦于资料受限,陈立基只能四处借来古籍孤本进行研读,希望从这些零星碎片、充满神话色彩的记载中了解三星堆遗址文化。期间,一些专家、学者口中有关三星堆遗址的有趣故事,便成为陈立基以后创作三星堆主题文学的素材。
资料收集并非易事。一天,陈立基听说四川省图书馆有一本《四川上古史新探》,书中内容对解密三星堆很有益处。为解疑,他专门前往成都借阅,但当时图书馆对此类书籍有规定,不允外借。怎么也不能空着手回去,没有办法,陈立基只能花费更多精力在图书馆阅读。
从薄雾弥漫的清晨,到落日昏昏的傍晚,那几天,除中午外出吃饭,陈立基将自己所有精力都沉浸在对此书的研读中。同时,他随身携带纸笔,不时进行摘抄记录。很快,300多页的《四川上古史新探》就这样被研读完毕,陈立基从中获益良多,受到很多启发。

2019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陈立基参加广汉市组织的签名赠书活动(陈立基 供图)
自“话”家乡史
1992年,一座现代化的专题性遗址博物馆正式奠基筹建。陈立基对此深感兴奋,以往的研究探寻已让他对三星堆文化着迷,更不要说这么一座专门展示三星堆遗址的博物馆。
耗时5年建设,博物馆于1997年10月建成开放。开馆仪式中,陈立基作为首批参观者踏进馆内。辉煌神秘的吊顶、气势宏大的兽面铜具、举世瞩目的青铜大立人、象征着人神合一的青铜神树、工艺繁复的青铜礼器等珍贵罕有的历史文物一一呈现在他面前。凝睇着回廊处的文物工作照片,陈立基清晰感受到这一历史遗迹为自己带来的厚重感和震撼感。
那是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历史沉淀,古代先人们的生活、文化、习俗、宗教、精神通过器具流传至今,参观者无不深受触动。然而在参观过程中,陈立基敏锐地察觉到,参观的游客虽惊叹文物带来的美,却并不了解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和历史。当时博物馆内解说人员还未上岗,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渊源晦涩难懂,出场馆后,很多游客抱怨馆内提供的资料太少,无法深入了解。
见状,陈立基想起培训班老师的叮嘱,三星堆遗址是自己家乡的珍宝,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他有责任通过文学发扬这一遗址文化。这一念头就这么生根发芽,加上省作协和省市领导也很支持,陈立基决心将自己对三星堆的想法和理解写成一本书,供世人更好地了解三星堆文化。
书写三星堆意味着开辟一条新道路,陈立基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和以往资料的汲取不一样,这次写作过程繁琐艰苦,好在有多年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积淀,陈立基耐着性子投入创作,细心撰写和打磨稿件。
几个月后,《日落三星堆》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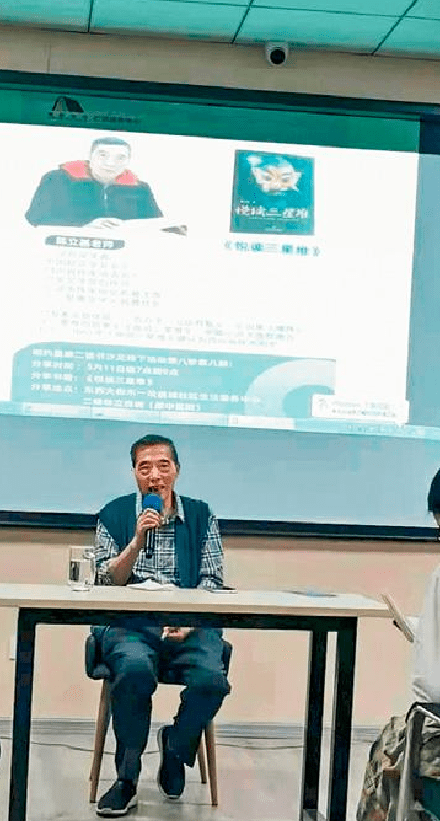
2021年5月17日,“相约星期二读书沙龙线下活动”第八季第八期在广汉市雒城社区生活服务中心举行,陈立基作为主讲嘉宾参加(陈立基 供图)
事到万难须放胆
1997年,陈立基创作了自己第一本讲述三星堆文化的书籍。他将自己了解到的本土资料,以忠于史实的方式讲述出来,又在后半部分收录一些关于三星堆的古诗片段和自译的文言文,内容详实,让人眼界大开。
令人意外的是,《日落三星堆》并未赢得出版方的信心。大部分出版社对初出茅庐的陈立基及他创作的三星堆文学不感兴趣,认为这一类型的作品没有市场前景,纷纷拒绝其投稿。
“事到万难须放胆”,看着自己创作的书稿,陈立基不愿放弃,既然出版社不出版,就算自费,也要将此书出版出来。定下心来,陈立基当即找到广汉当地的一个印刷厂,将自己所有积蓄都投进去,自费几千元刊印了2000多册《日落三星堆》。
对于书是否能卖出去,陈立基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写书的初心很简单,就是对三星堆文化进行记录和发掘,希望通过文学来增补三星堆遗址的内涵。
书籍印刷完毕,怎么售卖?陈立基想到三星堆博物馆附近的摊贩。当时游客参观完三星堆博物馆,多会在小摊贩处购买些当地特产。陈立基便请摊贩们帮忙代销图书,想着能卖出去就好,找回一些损失。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日落三星堆》一亮相,便受到极大欢迎,经商小贩、远来游客都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当时很少有这么具体阐述三星堆的文学书籍。
短短两三个月过去,《日落三星堆》售卖一空。陈立基十分欣喜,自己自费印刷的书不仅没有亏损,甚至还帮他赚了3000元,要知道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才几十元钱。
第一本三星堆文学书籍的成功给予陈立基很大鼓励,他开始明白这是一件大有可为的事业,也意识到有关三星堆文化的文学作品匮乏。作为长江文化发源地之一的三星堆,毫无疑问有着与生俱来的文学潜力,在此基础上,陈立基开始创作《三星堆的故事》一书。该书1999年由巴金文学院出版,如期收到市场积极反馈。
两本三星堆文学书籍俘获了众多读者的心,读者意见陆续寄到陈立基手中。其中,有读者建议他将三星堆的故事讲述得更生动形象一些。期间,出版社也和他商讨该如何深化三星堆文学,因为传统科普文学太过专业,读者不太愿意看。发现这一问题后,陈立基开始尝试用散文形式将三星堆文化具象化、趣味化、生动化。
在不断尝试和改进中,2000年,陈立基出版了散文集《趣说三星堆》。该书不同于前两本小说集,以散文的体例优化历史文学的弊端,将神秘古蜀国故事融入优美隽永的词句中,深受读者喜爱。据统计,《趣说三星堆》总计印刷11次、发行28000册,该书2001年11月被评为四川省优秀图书,2002年获德阳市第三届“五个一工程”奖。

陈立基送书进校园(陈立基 供图)
作家的长情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陈立基受到很多人鼓励,其中三星堆博物馆人员的帮助对他的创作启发尤为关键。当时新出土文物资料较为机密,普通人没有深入了解的机会,考虑到陈立基此前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宣传,博物馆对陈立基很优待,时不时会将有关三星堆遗址的公开资料分享给他。受此厚遇,陈立基也常协助博物馆进行接待和外宣工作,有外地作家来广汉参观,博物馆也会邀请他陪同。
就这样,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在博物馆的接待和陪同工作,也间接地开阔了陈立基的视野。他发现,作家群体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理解是深刻的,陈立基至今仍记得散文家席慕蓉来广汉参观三星堆时的场景。那天临近中午,一行人来到青铜神树展区,柔和下垂的枝叶、跃跃欲试的小鸟、蓄势待飞的神龙,恣意盛放的整体形态通过锈绿的青铜遗留下来。席慕蓉目不转睛地盯着青铜神树,驻足欣赏,久久不愿离开。在陪同参观的陈立基提醒她要中午就餐后,这位有自己悲欢离合、苦辣酸甜的作家,在去餐厅的路上又莫名地跑回展区,围绕着神树再鉴赏了一番。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这件事给陈立基留下深刻印象,作家群体对于三星堆古老文化有着天然的热爱。他相信,神秘和怪异是带有震撼力的,对文学创作大有裨益;反过来,文学创作也能将三星堆文化和其他中国古老文化发扬光大。
随着广汉三星堆遗址不断挖掘,“用文学发掘三星堆”的口号成为当地文学创作者的主题。借此,2003年1月,陈立基与广汉市作协同仁自筹资金创办《三星堆文学》杂志,收录大量关于三星堆的散文、长诗和剧本。此后10多年来,陈立基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众多稿件。借由三星堆,他也在不断磨炼自己,收获颇丰。
近几年来,他又陆陆续续创作《悦读三星堆》《穿越时空的对话》等作品,以及各类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近百万字。散文《表婆婆》收入《建国五十年四川文学作品选》,散文《三星堆飞天神曲》荣获2005年获四川省文联天府文学奖二等奖。除文学创作外,陈立基还携手三星堆博物馆学术研究部部长吴维羲进行相关影视创作的撰稿。2021年3月,他的图书作品又被录作音频,得到进一步宣传扩散。
笔耕不辍几十年,三星堆文化成为广汉的城市元素,陈立基也从中收获成功的喜悦。在一次文学论坛中,一家杂志编辑向陈立基表示感激,因为《趣说三星堆》带给他很大启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师也曾写信向陈立基表示感谢,认为他的著作在某些方面奠定了三星堆文学的基础。文学交流不分国界,首尔大学一位汉学家也曾致电陈立基,询问是否可以使用他著作中的内容与图片;对此,陈立基欣然允诺。
出于对三星堆文化的热爱,当初的尝试成为陈立基大半生的追求,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去三星堆博物馆参观。有人很奇怪,他至少去博物馆三五百次了,为什么每次还有这么大热情。陈立基却没有这种疑虑,他说每次到博物馆门前,遥望着馆内的珍宝,自己总是忍不住走进去。每次参观都有不同感悟,如何讲述上承千年的故事?如何诉说古蜀先民的期盼?如何描绘苍茫高山的文化迁移?他都在每一次参观中得到灵感。
多元文明走向未来
现今早已不是几十年前,为一本资料远行的年代,越来越多三星堆文学争奇斗艳,现代科技将文学创作的界限抹除。陈立基从事三星堆文学创作几十年,对此类文学推陈出新之法独有建树。三星堆文明同中华早期文明的主流黄河文明,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但它也正诠释了华夏文明多元化的本质。与此同时,如学者朱大可所提出,三星堆文明是部分独立于主流文明,这也导致它是孤独的。
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是理性式的探索,我们将文物归纳、将遗迹保存,解读纵目面具的符号特征,分析青铜神树中的文化内涵……但考古界的工作仅限于此,也只能到此为止,深入抓取三星堆文明的灵魂需要文学界的触摸,要填满主流文明和三星堆文明之间的鸿沟,需要用多元化的文学创作释放它的孤独。
因此,陈立基提倡现代三星堆文学乃至其他非主流文明的文学要以更加多元化和多角度的方式呈现,作者和编辑甚而可以采用针对性的指向功能扩充单一文学创作的可容纳性,推出少儿版本、青少年版本、成人版本,从科幻、动漫、画册等角度揭示这些独属于华夏文明的历史。
关于创作细节,陈立基也提到很多,“随时想到读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三星堆文学创作需要规避读者的阅读障碍,例如将古文趣味性地翻译成现代文,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增加可读性,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伫立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遗迹很可能是人口迁移、文化传播的果实,现当代文学创作者需要做的是打破果实孤独的外壳,暂时性地放下学术体系带来的天然壁垒,重建千年历史和当代文明的联系,直接用灵性同三星堆文明对话沟通。陈立基老先生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透过他的著作,我们可以窥见万物的兴亡盛衰,代表着华夏古老文明的青铜神树以昂扬的姿态朗照古今。
择一事终一生,文人风骨,作家豪情,陈立基正用自己一生去推动现代三星堆文学的发展。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