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论杨慎对道教的智识化审视与体认|| 范靖宜


论杨慎对道教的
智识化审视与体认
范靖宜
杨慎对道教秉持“不以怪力乱神”的儒家知识精英的一贯立场,即汲取道、佛中宇宙论、天道自然论及心性论等论述,忽略甚至贬斥教义、仪式以及超自然现象等相关内容。而杨慎对道教著述进行了一定诠释,试图将他认为渺远虚妄的神仙之学导向性命之学。本文即对杨慎审视道教的智识化态度及其后期的具身体认进行分析与论述。

一、 杨慎的道学观综论
对于道家学派的学说,杨慎没有专门阐发《老子》意旨的著述,而世又传他曾著有一部解庄的专著《庄子阙误》。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16、《明史·艺文志》卷98与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子部》都有相关记载。另外,《八千卷楼书目·子部》卷14、《续文献通考》卷175等则将《庄子阙误》归入焦竑名下。李调元在撰写《庄子阙误跋》时误以为焦竑将《庄子阙误》纳为己有:“竑有《庄子翼》八卷,末亦载《庄子阙误》一卷,不题升庵作,直据为己有,明人好袭,竑尚不免,他何论乎?”据邹阳考证,《子书百家》(《百子全书》)本《庄子阙误》序没有再指责焦竑将《庄子阙悟》据为己有,原因是此序为后人发现李调元失察,然后修正了李调元的意见。同时,邹阳也提出《庄子阙误》是杨慎本人改写还是书商托名伪撰已不可考。
杨慎对老庄思想的解读与诸家解庄的辑录集中收录在《谭苑醍醐》卷1与《太史升庵文集》第46卷,另外散见于“丹铅”诸录的学术笔记中。其中,“庄子解”较为完整的版本收录在焦竑所编录的《升庵外集》中,是焦竑以《谭苑醍醐》中“庄子解”部分的条目为底本,辑录了其他散见于杨慎作品集中的笔记而成,共73条。
在“大礼议”之后,杨慎通过重新诠释老庄思想对儒家的核心价值仁、礼、义等都进行了重新审视,通过儒道互补思想调适身心。而杨慎的道教观究竟如何历来众说纷纭,意见未能画一,其讨论皆围绕着《洞天玄记》而展开。然而,随着研究推进,目前认为《洞天玄记》应非杨慎所作。那么杨慎对道教究竟持有何种态度?其到滇南后创作的诸多游仙诗是否只是对舛途的一时抒怀?其与诸多世外隐者的交游是否只是文人的雅集酬唱?这就需要对杨慎的著述作综合全面的考察才能透视一二。他在《古文参同契序》中道:
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是为务,则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人之所以教也。
杨慎借班固之语道出了他对神仙之学的看法:学习神仙道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周全性命,探求生命之真。道家与道教将得道之人称为真人,如《庄子·大宗师》载“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但是杨慎在此也强调了一个度的问题,若是过分钻研沉迷如养身炼气、内外丹道一般的道术,不仅使世上诡奥难懂之书越来越多,也与圣人教化之旨渐行渐远。可以看出杨慎对道教性命之学是抱有肯定态度的,但不赞成向外对有为之法的无止境求索,认为“游求于外”的最终目的是认识世界,进而合于大化,消除内心恐惧。这可看作杨慎道学观的总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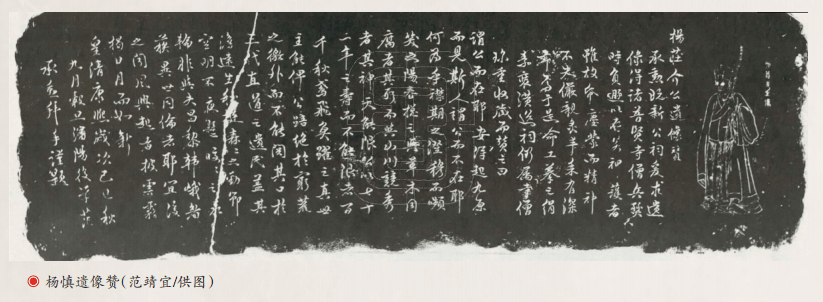
二、杨慎对道教的智识化批判
杨慎借班固之口道出中国古代大部分持正统观儒生的基本态度:对神仙之学展示出好奇与兴趣的同时,也时刻提醒自己与其他正统士人不能抛却经世之业。因此,宋代以降士人对《悟真篇》等主张三教融通的修养性命之书的兴趣已远远超过外丹、斋醮符箓与保存有古早方术影子的道术。这反应了众多士人对内在超越的渴望远超外在肉身的解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便如杨慎在丹铅诸录中所严厉驳斥的那样:神仙怪谈被大量用来误导无知百姓,诱使他们信仰并朝拜虚无的神灵以获得短暂的精神安慰,最终造成百姓人财两空,背弃了宗教的教义与初衷。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儒生如果也听信这些怪谈则枉受圣人教诲,不免流为笑柄。其二是经过唐宋时期的三教合流思潮,确实有许多士人对道家老、庄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其视为儒家学说的调和剂。其中老子的学说偏向于政治哲学,庄子之学则多言内在精神的超脱与心灵的自由。老庄之学虽然被认为是消极避世的,但二者都追求虚静的境界借以达到最终的大道与逍遥,这给以入世为目的的儒生提供了暂时的精神安宁,也使大多数儒生视虚静坐忘为涵养工夫,把内在的超越当作如同内圣一样的最终目标。“穷理、尽性、了命”这一思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儒家对于内圣追求的程序。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省略,但是理学对于尽性、了命都没有像佛教与道教一样步骤分明、内容完整的工夫体系。以程子为例,对于如何尽性至命,其只说“尽孝悌”便是。程子此意是性命孝悌在本体上是不分轩轾的,强调二者的体用一如,但这只是本体上的认识,却无法给予人在实践上的具体指导。
问:“行状云:‘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不识孝弟何以能尽性至命也?”曰:“后人便将性命别作一般事说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统底事,就孝弟中便可尽性至命。至如洒埽应对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统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后来人言性命者别作一般高远说。故举孝弟,是于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时非无孝弟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无论程子之“命”的内涵是命运还是生命,终究还是没有讲清楚此间的次第。朱熹可能是意识到儒家了命工夫的欠缺之处,故而作《周易参同契考异》。然而从朱熹化名名“空同道士 邹”这一行为可以解读出的是,儒生对于文化身份是十分谨慎、不敢轻易逾矩的,像张商英、赵贞吉这样可以公开自己宗教信仰与参禅打坐等身心实践经历的儒生仍然是少数甚至异类。可以说,愈是在学术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儒家学者在参与与佛、道有关的事物时愈加隐晦。儒生与教内人士虽然在欣赏自然山水、追求艺术审美等方面拥有相同的志趣,但在学术理路上终究是“异门”。杨慎对很多人亲眼见证的唐代女仙谢自然成仙事件的态度反映了他对宗教中神异部分的否定,甚至批评了韩愈的轻信:
韩文公不信神仙,而《谢自然》一诗亦信以为有,盖当时有人的见,而公亦的闻也……以此观之,谢为道士所惑,染其妖术飞升之事,如今时术人骑草龙上天之类耳,是昌黎亦为所欺也。世又有病风颠者,即能乘危升高,疾愈即不能矣,谢自然宁非此流耶?……是以圣人不语怪,而异端之士,君子深恶而痛绝之,亦以避祸而远辱也。
神异现象向来被儒家正统斥为异端。如《近思录》专辟一卷收集二程等人对佛、道虚妄之说的反驳。杨慎于此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谢自然升仙之事作出解释,并发现以反佛著称的韩愈虽专门写诗斥责谢自然冲举是“从物迁”——即违背了人伦常理而妄想长生,但其实只是对此事意义的批判,而本质却没有质疑此事的真实性。杨慎认为韩愈在此被江湖道术迷惑了,并分析了此中骗术的关窍。韩愈对飞升冲举事件真实性的存而不论,抛开道教在唐代为国教的文化影响与科学认识的局限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韩愈对宗教信仰态度的微妙之处。韩愈虽以排佛反道著称,但被贬潮州以后却写有《潮州祭神文五首》《曲江祭龙文》《祭竹林神文》,并发明了新的祭祀对象“界石神”。虽然有学者认为韩愈的信仰只是原始的自然宗教信仰,是“基于儒家的一种利人的伦理思虑”,但这确实显现出韩愈某种价值取向上的倾斜。杨慎对韩愈的批评除了表现为一种对儒家正统观的再伸张外,也是其求真求实的科学理性思维的缩影。
杨慎客观中正地评价了儒释道人物在诠释自然现象时是否具有理性意识,从这点也可看出他对道教及教内人士肯定的一面。如在“宋儒论天外”条中他评价宋儒是不知“天”而强言:
《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云:“日入地中,构精之象。”后人遂谓日昼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长春曰:“轻清者上腾为天,重浊者下凝为地。万物有形,重浊皆附于地;三光轻清,悉上于天。既上于天,如何却沉于地乎?且星陨于地而化为石,古今有之。星坠于地犹化为石,况地下乎?……”明夷之卦,文王拘于羑里,失势之象,何足为据?右丘长春所论如此。愚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类。邵子“构精”之说。元儒已讥其亵天。由此观之,长春之识卓矣。
邵雍与丘处机都是从各自的身份出发对《周易》中明夷卦进行诠释。邵雍为易学家,故以“构精”说阐释;丘长春身份为道士,故从轻清者上升、重浊者下降的道家宇宙生成论出发对太阳是否入地进行解释。虽然丘长春理论的出发点与角度仍与道教有关,但是他的分析是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杨慎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杨慎对丘长春的推崇代表了他认为儒释道在认识自然规律与求真之路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三教的起始点都是相同的,并不因为儒家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所有论断就应该是正确的。这是杨慎对儒家的批判之处。从这里也可看出,《周易》是杨慎融通三教的一个枢纽。从儒释道对《易》的诠释中,杨慎可以直观地判断谁是其中的合真合实者,并借此对程朱等宋儒之学的荒诞之处直接展开批判。在“大礼议”前的半生里,一种文化身份的视角似乎阻碍了杨慎的某种远见卓识,或是其碍于身份对宋儒的错误之处存而不论。但“大礼议”后杨慎反而解除了思想上的禁锢,对宋儒表现得越发不以为然。他开始对过往的自己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不止于对程朱以及邵雍这些学术潮流引领者的言论的正当性,还有对受理学禁锢的一般俗儒的“不学无术”的嘲讽。此时,教内人士又成为其对比的参照物,在“丘长春梨花辞”条他写道:
长春,世之所谓仙人也,而词之清拔如此。予尝问好事者曰:神仙惜气养真,何故读书史作诗词?答曰:天上无不识字神仙。予因语吾党曰:天上无不识字神仙,世间宁有不读书道学耶?今之讲道者,束书不看,号曰忘言观妙,岂不反为异端所笑耶!
杨慎认为像已达到丘处机这样境界的高道尚且拥有拔俗的创作水平,可见读书反而有益于出世者的养性修真功夫。他戏言道神仙都无不识字者,借此讽刺当时奉行心学的一些儒生只知束书追求心悟,在闻见之知的积累方面尚不如方外人士,反倒成为异端。
以上杨慎对道教的智识化审视是从学理与认知角度出发的。而对于道家与道教的出世情怀与隐逸情节,杨慎是在滇南的不断体认中逐渐变得心有戚戚。若说老庄思想使其以佯狂的姿态走向了对“礼”的解构,那么道教的出世情怀则使其痛苦、徘徊的精神得以安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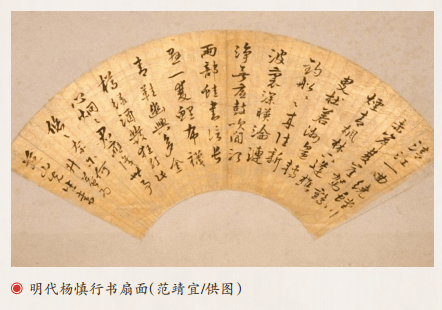
三、杨慎对道教思想的具身体认
杨慎对道教出世情怀的体认多反映在其游仙主题的诗词作品中。这些作品有一部分是其在痛苦的情绪之下暂时的托言纾解,并非真想要游仙归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晚年的一些游仙作品中已经映射出他对身患焦虑的某种真实思考。如《春兴》其八道:
天上风云此际多,山中日月竟如何。
争传鸣凤巢阿阁,又见飞鸿出罻罗。
宣室鬼神思贾谊,中原将帅用廉颇。
难教迟暮从招隐,拟把生涯学醉歌。
“招隐”始出西晋左思《招隐诗》,描写了诗人的隐居生活及不愿与俗世同流合污的心情。后“招隐”题材诗在两晋蔚然成风,《文选》中多有收录。杨慎在晚年以前从未放下复仕的期待,就算他已认清嘉靖皇帝挟私报复之心,但仍希望可以回乡终老。正所谓无欲则刚,在有所求的心境下,杨慎无法做到真正的高隐,只能放浪形骸来避祸兼了此残身。而在这两种原因之外,身老多病的杨慎也认识到自己已无法追求真正的道教仙隐,表现出幽微的身患意识。他在《周彦通侍御秋斋(二首)其一》中将仙隐与吏隐区分得十分清楚:
北斗临茅宇,西山出蕙楼。
凉风吹玉树,明月下金丘。
歌对梧桐语,辞因丛桂留。
高人耽吏隐,不是采真游。
杨慎将周彦通的隐逸定义为吏隐,区别于“采真游”——即道教出于求仙修道目的的隐逸。从首辅之子到状元及第,从长安街上对月吟唱弹词的相国公子到御前的经筵讲官,杨慎“大礼议”前的人生经历春风得意。除了几次丁忧致仕及对皇帝行为不满托故回乡的不得不隐之外,杨慎的人生是与隐逸很难产生关联的。来到滇南后,道家给予他的精神能量主要体现在山水对他的治愈与佯狂避祸的行动中。但是与多数仕途失意的文人不同的是,他并没有主动选择做一名只知耽溺于山水的沉潜隐士,而是投身到著书立说、交友结社、兴办教育的入世事务中去,以儒家的使命感去化解不幸。所以,杨慎对于道家式的隐逸虽赞叹但不效仿。但随着年岁的增长,杨慎对道教之隐逐渐产生了思考与兴趣。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将身体看作窥见大道中的需要跨越的障碍。道教相比道家更强调在坐忘的虚静中身体的具体解脱次序、方法及克服生命自然性的逆向生命意识与身体实践。杨慎在云南与自然的互动中忘却尘俗机变,疗愈“大礼议”以来的创伤。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身体衰朽,杨慎不得不又从老庄哲学给他带来的心灵平静中跳出来,对身体进行更深的思考。其晚年曾多次遭遇疾病,徘徊在生死之间。仕途所带来的身世荣辱已被疾病的困扰所消解,普通的隐世及与自然的互动慢慢不足以消除他对身体以及生死的焦虑。此种境遇促使杨慎对道教思想又产生了新的体认,也深化了其晚年在治学中的儒释道融通倾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范靖宜(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