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在中西比较、文明互鉴中寻求文化自信之根
在中西比较、文明互鉴中
寻求文化自信之根
——专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曹顺庆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曹顺庆(右)与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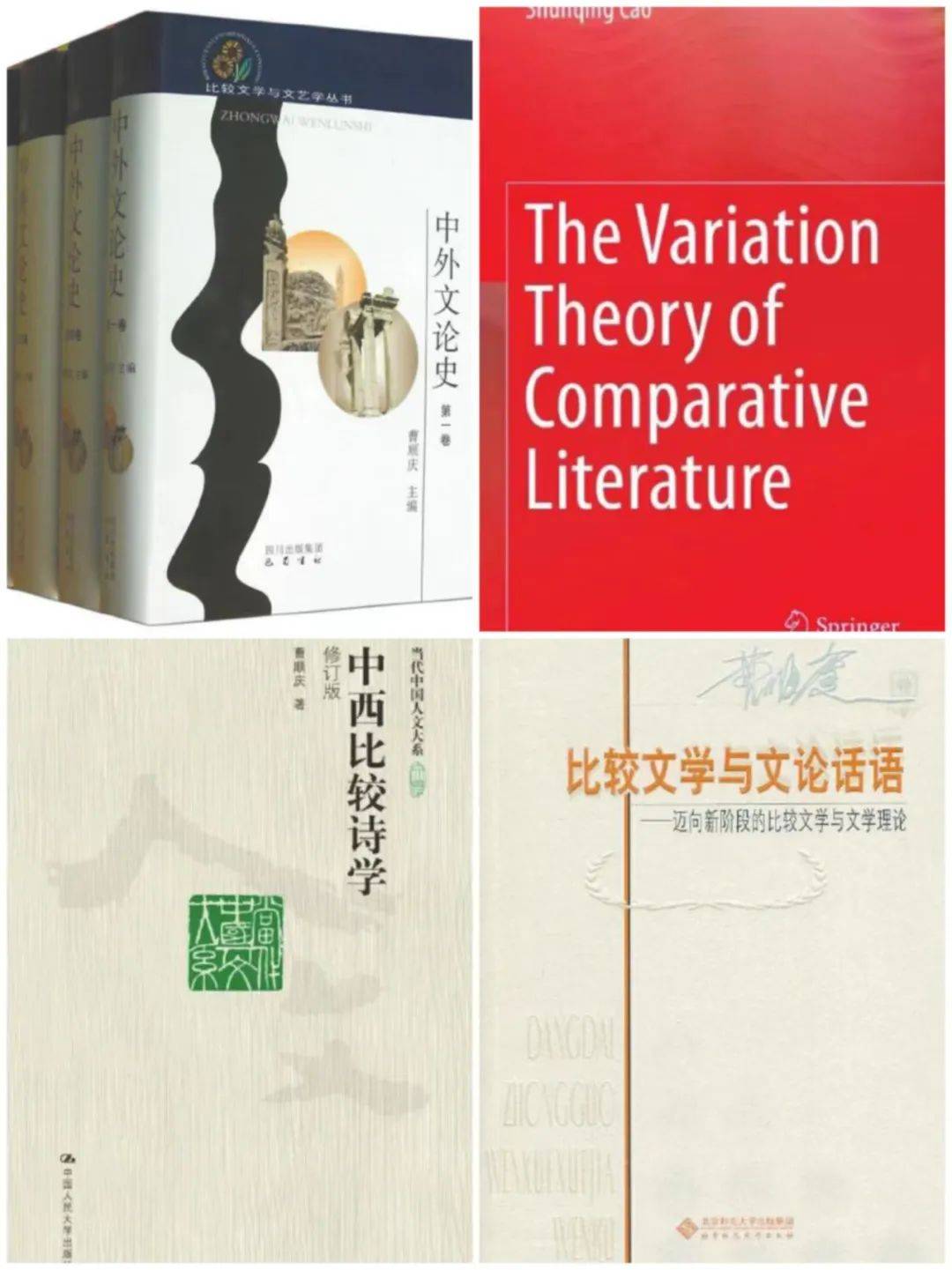
曹顺庆出版的著作
国内人文学者要夯实知识底座,主动发声并积极介入国际主流学术话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文明进步其实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成果。学问是世界性的,中华文化不能只是中国人讲,最要紧的是国际传播、国际理解,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应该建立在跨文明的基础上。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曹顺庆,不仅是一位精力旺盛的人文学者,也正在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被研究对象”。
近日,学术期刊《文艺争鸣》邀约6名中外著名学者撰写论文,将集中探讨曹顺庆提出的“失语症”、比较文学变异学、中国文论话语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等论题;2024年2月17日,在他年届七旬之际,“曹顺庆先生学术思想暨中国话语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线举行,吸引了海内外3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2023年,中国香港出版的《文学跨学科研究》推出曹顺庆学术研究专栏,刊登了法国索邦大学教授佛朗科等人的6篇学术论文……
曹顺庆的学术生涯,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起步,随后逐步进入“中西比较”:中西比较诗学、“失语症”、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卡嗓子”问题和“重写文明史”……尽管身处西部内陆,曹顺庆与其带领的学术团队却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聚焦中国文化。近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曹顺庆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取向与之不谋而合。他说,国内人文学者要夯实知识底座,主动发声并积极介入国际主流学术话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言说自身的文明观、重写文明史
2024年2月17日,“曹顺庆先生学术思想暨中国话语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来自中、美、英、法、匈等国的300余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云端,共同探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重要议题。
此次研讨会一大关键词“中国话语”,与曹顺庆近30年前提出的“失语症”遥相呼应。1996年第2期《文艺争鸣》杂志,刊发了曹顺庆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响与讨论。他在文中说,当前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
意识到这是中国学术乃至文化面临的困境,曹顺庆后来的学术探索,几乎一直沿着这一思想脉络展开,不过即使到了今天,“失语症”仍未解决。前两年,曹顺庆受邀参与编纂《牛津文学理论百科全书》,收到书后他发现整整四大本,关于“中国文学理论”只有自己编写的一条。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西方文学理论一个流派的一个术语,如“Close Reading”(文本细读)就有单独的词条,“其分量与古往今来整个中国文学理论并驾齐驱,这显然不合理。”
曹顺庆将其形象地总结为“卡嗓子”问题,即别人让你“说不出来”,乃至你自己根本就没想到要说出来。在他看来,怎么样“打开嗓子”是当代学术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也是真正重建文化自信的关键一环。
因此,2023年初,在由四川大学等主办的“文明书写与文明互鉴”高峰论坛上,曹顺庆提出“重写文明史”的号召,并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长篇论文《重写文明史》。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已经进入新的变局和多元格局之中,我们必须对世界格局和文明互鉴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重写文明史”就是一次主动发声的机遇,中国学者应借此言说自身的文明观、书写自身的文明史,由此延伸到各个学科史,构建文明新话语,献策于当下的文明互鉴和全球治理新格局。
以世界性眼光探索“中西比较”学术路径
实际上,从学术生涯之初,曹顺庆就开始关注“中国话语”。1977年,曹顺庆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学习,逐渐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学术理想,为了求得名师指导,此前从没来过四川的曹顺庆,慕名考取了四川大学中文系杨明照先生的研究生。
研究生求学经历,曹顺庆至今印象深刻。“杨先生讲《文心雕龙》,首先背一遍原文,然后再逐句讲解;杨先生的书桌上,永远放着《十三经注疏》。”前辈学者博大精深的学识,深深激励着他。
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一门心思想搞古代文论的曹顺庆却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当时一些学者用“内容-形式”来剖析《文心雕龙·风骨》,有人认为“风”是形式、“骨”是内容,有人认为“风”是内容、“骨”是形式,有人主张“骨”同时包括了内容的充实和形式的严整。后来他意识到,“风骨”作为一种中国文论独具的极有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一旦被外来的“内容-形式”话语切割,便容易产生各种互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观点。
后来,在杨明照先生的鼓励下,曹顺庆开始探索中西比较诗学的学术路径,相继发表了《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与孔子的“发和说”》《“风骨”与“崇高”》等多篇论文。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继续师从杨明照,以“中西比较诗学”为主题开展博士论文研究,不仅成为四川大学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生,更是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第一个博士生。
作为曹顺庆博士论文的评审专家之一,著名学者季羡林高度评价:“曹顺庆同志的论文既有宏观的观察,又有微观的探讨。他对中西两方主要的文艺理论流派都能了若指掌,论述起来,有极大的概括性,颇有高屋建瓴之势。他的论文确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有极大的说服力。”
这条“中西比较”的路径,从此贯穿曹顺庆的学术研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探索从微观的文论、文学直至宏观的文化、文明等主题,在不断地互鉴中寻求文化自信之根。
积极参与学术前沿活动,建立自身话语权
尽管已经年届七旬,曹顺庆的日程仍然排得很满,除了科研工作和学术活动,他还坚持为本科生、研究生授课,招收、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专业研究生。
曹顺庆认为,即使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也应该直接阅读古代典籍原著,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础。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带博士研究生起,他总会指导他们以清代阮元校注刻本的影印版为教材,系统学习“十三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博士生在课堂上背诵古代经典文论。
他也主张借助英语等语言直接学习西方知识,而非吸收国内学者“反刍”的二手乃至三手信息。给博士生讲西方当代文论时,曹顺庆采用的教材就是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英文原著《文学理论导论》。
曹顺庆发现,在比较文学学界乃至其他人文学科领域,有两种常见的情形:一些学外语出身的学者和学生,外语很好但不懂中国古代的东西,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往往外语又不太好,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很难“对撞”。唯有熟练掌握两门以上语言,兼通古代和现当代文化,才能有效地进行中西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当代世界学术前沿活动,中国学者也要积极参与,建立自身的话语权。”他表示。
这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应有之道。2021年初,四川大学正式启动“创新2035”五大先导计划,曹顺庆成为其中“文明互鉴与全球治理研究”首席科学家之一,聚焦人类文明多样性、汉语言文学与世界文明、古文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等话题展开研究。“我们要重写人类文明史,并进一步用文明交流互鉴来推进重写各个学科史,不仅用中文来写,也用英文来写。只有把被遮蔽、被曲解的文明事实纠正过来,人家才会口服心服。”
对话整个文明史应该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中西比较的根本想法是把中国文化说清楚
记者:您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曹顺庆:我1971年入伍,在贵州省军区文工团当文艺兵,拉小提琴、二胡、京胡,1977年3月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很有特色,有汉语言文字、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三个本科专业,我就被分到了文学评论专业。我们当时的校长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的翻译者陈望道,后来是数学家苏步青,他的文化修养很高,诗也写得好。我们在校的时候,郭绍虞教授、蒋孔阳教授、王运熙教授这些著名学者都还在世,他们和年轻一点的钱锺书先生的助手王水照,还有章培恒等很多老师都给我们上课。
在复旦大学,一方面是这些名师引导,另外一方面学校的条件还不错。我记得那时候图书馆是全天开放的,你只要进去不出来,没有人赶你走。有时候我就带一点干粮,在里面一泡就是一天。我把图书馆里面的世界史、中国史都看了,再进一步到中国哲学史、世界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然后再到文学理论。还有我们中国的典籍,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那时候当然还是半懂不懂的,不过毕竟看完了。我在复旦大学时间不长,但可以说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
记者:几十年来,您的学术生涯经历了多次研究主题、范式的转换,从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延展到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变异学,以及“失语症”“重写文明史”等话题。这种转换的内在动机和考量是什么?
曹顺庆:其实是学术发展使然。我刚来川大读研的时候,一门心思就想搞中国古代文论,但是我在读《文心雕龙》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跟着杨先生参加会议,听了不少学者发言,也看一些文章,却感到越来越糊涂。
记得我刚入学时,跟杨先生到广州开会,一个老先生在台上发言,讲白居易《与元九书》的现实主义特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一个香港学者当即反对,说《与元九书》是浪漫主义的。白居易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以情感才是他的理论根基,这是浪漫主义理论。大家就分成两派吵了起来,最后吃饭的时候都不坐在一块。
当时我就在想,到底是现实主义对,还是浪漫主义对,还是白居易本身就错了?后来我发现,为什么讲不清楚,因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从西方来的,当我们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论的时候,那就要出问题。中西方理论各有所长,但是它们的理论范畴、讲话的方式、阐述的方式都不一样。怎么样真正理解中国文论,同时又能跟西方理论结合起来,我意识到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给杨先生提出博士论文不单纯写中国文论,而是写中西文论比较,当时西方比较文学界已经把它叫做“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
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出书,杨先生专门写了个序,他很赞赏鲁迅所说的:“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他说鲁迅都这样强调,那么《文心雕龙》和《诗学》相比较,实际上也是当代学术界应该做出来的。所以在杨先生的包容下,我就走上了中西比较这条路,但根本想法是要把中国文化说清楚。
“失语症”事关我们的文化自信问题
记者:1996年,您发表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成为您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著之一,今天“失语症”甚至已经进入了公共讨论。当时写作此文的背景和动机,以及您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曹顺庆:开始做中西比较以后,我觉得很多学者的路走错了。错在哪里?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学术话语的问题,是西方话语和中国话语“打架”产生的问题。比如我们读“十三经”,有“春秋话语”,说在表述的时候要“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这一套话语跟西方差别很大。
所以当我们用西方话语来讲中国,或者反过来的时候,沟通起来都是有问题的,这就是“失语症”。比方说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用内容、形式,用典型形象、典型人物这些概念。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我们习惯这样讲,但中国古典诗歌,它往往既是写实,又是抒情,既是以情感为根,同时也在描述现实。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基本上没有讲清楚中国文学的话语,我们的文学史要“重写”。
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很精彩,本来它就是中国话语,但是这一套话语在今天是不能诉说自己的,不仅不能拿来解释中国文学作品,还不能解释自身。它在当代“死了”,因为大家都不用它,而且还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它。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个博士,但这个学科名称本身就是西化的,是literary criticism翻译成中文的结果。中国古代文论有“批”,也有“评”,但是“批评”两个字连用是没有的,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听不懂。
1994年我从哈佛大学回来,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篇文章投给《文艺争鸣》,很快登出来,引起很大的波澜,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当时我想,既然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就要说出来,这事关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事关中国当代学术发展,事关中国文化发展,甚至事关我们的文化自信问题。没有想到过了若干年,这个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记者:您从中国文论问题出发提出“失语症”,它的根子在哪儿?“失语症”与您近年来倡导的“重写文明史”有何关联?
曹顺庆:中国古代文论是世界三大文论体系之一,后来学术界却认为中国文学理论没有体系、模糊混乱;认为它虽然有价值,但就像散金碎玉一样,是零碎的、散乱的、直觉的、顿悟的,不是理性分析的,要用就得进行“现代转换”。其实中国文论肯定是有体系的,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李渔的《闲情偶寄》、叶燮的《原诗》,但是它跟西方体系不一样。当我们用西方体系来“切割”它的时候,就把中国文论切割“死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文明互鉴、文明交往的主体性问题,我们丧失了文明的主体性,让西方来言说我们,把西方理论当作“元话语”来“切割”我们的体系。正如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来讲李白、杜甫、白居易,讲不清楚。其实西方理论传进来之前,中国人讲不讲文学?当然讲,讲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讲“意境”,讲“言外之意”“象外之象”。
这是中国话语、中国文化的失落,这种“文化病态”是怎样形成的?一个根子就是文明的问题。从近现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大河改道”的过程,当我们落后、被动挨打的时候,觉得只有打倒传统文化,才可以获得新生。其中,有一些认识难免是片面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重写文明史”?我们读了一大堆西方学者写的文明史,挑出其中170多部仔细看,发现它们长期以来彰显西方文明的高明和东方文明的野蛮,有几部文明史甚至根本没提中国,或者认为中国文明是僵化的,没有进步。
人类历史上明明存在文明互鉴,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文明进步其实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成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写文明史”,只有厘清历史的真相,我们才知道全人类共同构筑了人类文明进步之路。没有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走不到这一步;当然了,西方文明也促成了东方文明走到这一步,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个文明史应该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而不是说一种文明是优越的,其他文明是野蛮的、落后的。这是一种“文明病态”,这种文明观必须被彻底改变、彻底颠覆。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要以跨文明为基础
记者:您曾经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它因何而生?其学术旨趣是什么?
曹顺庆:西方主要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是法国学派提出来的“影响研究”,一个是美国学派提出来的“平行研究”。我为了搞懂这个问题,主编了一本《比较文学学科史》,后来就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应该有的东西。应该说没有比较文学学科之前,并非没有比较,西方人把他们古代的一些东西拿出来比较,我们中国也有。比如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南北文学不同论”,当时北边是鲜卑族,南边是汉族,这就是典型的跨民族的比较。
后来我提出,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都认为同一文明的文学才可以比较,都没有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不同文明的文学可不可以比较?其实在西方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前,中国就有很多人搞这样的比较,比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现在都算比较文学。这其实是文明使然,我们在不同文明碰撞的时候产生文明危机感,必然要进行优劣比较、异同比较。今天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的比较文学时代,但是全世界的比较文学是不合格的,因为它没有解决跨文明的问题,所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应该建立在跨文明的基础上。跨文明有“同”也有“不同”,“不同”怎么比较?我提出,“不同”是流传中的不同,任何一个文学作品,任何一个文化现象,从一国流传到另外一国,就会产生变异,就会产生差别。英国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莎士比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赵氏孤儿》和西方的《赵氏孤儿》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会变异。我就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作为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方法,后来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前主席佛克马的建议下用英文写作出版,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写进了国外的一些比较文学教材、专著。
记者:跟您研究领域的多元性相似,您的不少研究生也具有跨学科背景,在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承上,您是如何考虑的?
曹顺庆:我觉得只搞一种学问,是不能真正搞好的。我们今天培养人才,需要知识既扎实又广博,尤其现在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就很难产生孔子、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我主张学问要面面俱到,有广阔的视野,才有真正的创新。我指导的学生,有学外语的,有学古代文学史的,有学现当代文学史的,还有学音乐的,五花八门,我让他们互相学习。这种“多学科”“全面学问”是我的基本思想,我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学者,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
学问是世界性的,中华文化不能只是中国人讲,最要紧的是国际传播、国际理解。我们搞学术,其实有现实意义,西方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或者说“跟西方文化不同的文化也优秀”是要打个问号的。中华文化要让全世界认识到,只有不同文化共同推进,才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我们要研究全世界在思想融汇、文明互鉴中取得的突破,其中既有西方思想的功劳,也有东方思想的功劳,才会真正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文明“行”,中国文明“也行”,全世界的文明“都行”,如果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人类的文明就是光明的,这是我们人文学者的历史使命。
记者手记:冲破文化中心主义的藩篱
从2006年到2013年,我都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求学,其间,曹顺庆教授一直担任院长。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徐新建教授则是曹顺庆教授20世纪90年代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不过,对于这位“师祖”的学术研究,我却并不十分了解。因此,这次采访就成了迟到的“补课”。
完成采访,写出稿件,我忽然明白了大学期间的一些事情。比如,为什么川大会开设校级必修课《中华文化》,并由曹顺庆教授主编同名教材;比如,为什么文新学院会有《文化原典导读》课程,一学期精读一部《老子》《世说新语》《维摩诘经》这样的传统经典;比如,为什么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乃至文学理论教材,满篇都是不太容易消化的原典原文;又比如,为什么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强调“跨学科”和“兼通”……我想,原因在于前辈学者的学术实践和研究成果表明, 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此基础上贯通、融通、会通和比较,方有助于我们冲破文化中心主义的藩篱,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人类的文化、文明成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交流互鉴。
这一点,曹顺庆教授无疑作出了表率:他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也精通西方古代和现当代文论;他的师友中,有杨明照先生这样的传统学问研究大家,也有宇文所安教授、佛克马教授等国际汉学、比较文学名家;甚至上大学前在部队文工团,他也是既拉小提琴,也拉二胡和京胡……
我想,这也是我们谈论文化传承发展、探索文明交流互鉴时,应该具备的一种多元视野。正如川大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示,当我们具备了广博和开阔的知识底座,真正的创新才可能从中产生。
人物简介

曹顺庆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
5次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次获四川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6次获一等奖,5次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5次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奖。
担任CSSCI辑刊《中外文化与文论》主编,国际英文刊物Comparative Litera-ture:East & West(ESCI,劳德里奇出版社出版)主编。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40余部。

来源:《四川日报》2024年8月6日第5版
作者: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