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巨流河流到乐山:寻觅齐邦媛读书之地‖蒋少龙
巨流河流到乐山
寻觅齐邦媛读书之地
蒋少龙

在国立武汉大学西迁纪念碑前合影(前排左一系本文作者)
笔者有篇文章专门写抗战时期的大学迁川,题目是《华西坝、沙坪坝、古路坝:抗战时期的三大坝》(见公众号《永远的华西》,2024年2月27日“方志四川”等公众号转载)。其实,除了三大坝外,抗战时期迁川的大学还有国立武汉大学迁往乐山、国立东北大学迁往三台等。
2024年3月28日凌晨1时,《巨流河》作者齐邦媛去世,享年100岁。她当时就读的大学,就是已经迁往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
齐邦媛在80多岁时完成的自传《巨流河》,最为华人读者所熟知。这部25万字的回忆录于2009年首次在台湾出版,201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作品由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写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为两岸留下一部“至情至性的家族记忆史”。
2024年4月中旬,众友乐山李庄行,专门造访乐山师范学院、乐山文庙等武汉大学迁川遗址,寻觅齐邦媛先生当年读书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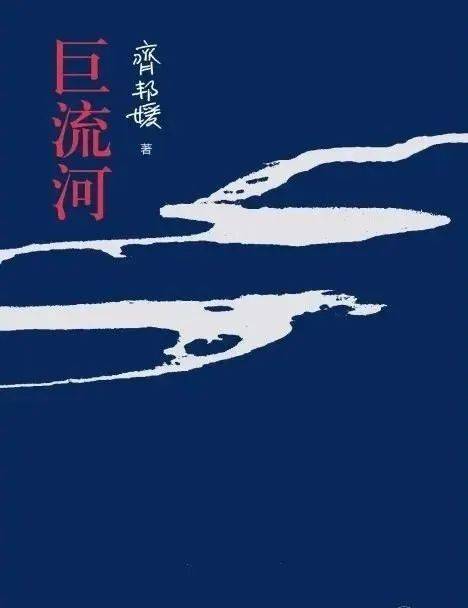
我们在乐山师范学院校园按图索骥。进入学校大门,右转走过一段缓坡,气喘吁吁地爬上一段石阶,再往右走望见路边高处平台上矗立着一雄伟的石碑,周围绿树环绕,庄严肃穆。碑顶端刻有“武大”二字,下书“1938——1946”,碑身中央竖刻着“国立武汉大学西迁纪念碑”。

齐邦媛就是在这里读大学的。她高中就读已经迁往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高考时选择的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哲学系,之所以如此,是幼稚地想向父亲挑战:你到德国读哲学,我至少也可以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探索人生深奥的意义。

但她却被第二志愿的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录取了,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竟在发榜后不久,来信通知南开说她的英文分数高,欢迎她前往就读。但她执意“追求真理,思考人生”,决心读哲学系。谁知一年后在武大受朱光潜老师劝告,仍转入外文系,一生命运似已天定。
人生恰似巨流河,终其一生,人生、真理似乎都非自己思考能解。
1943年8月底,她由重庆溯江前往川西嘉定(乐山旧称嘉定府),住在位于乐山白塔街的武汉大学女生宿舍。在此一住就是将近十年,八年在战时,两年在胜利后“复员”初期。当时宿舍的设备很简陋,都是晚上九点熄灯,但气氛大不相同。大学宿舍当然比较自由,在熄灯前可自由出入。乐山白塔街的女生宿舍被称为“白宫”,是一幢木造四层楼建筑,原是教会为训练内地传教士而建的,所以勉强可以容纳百人住宿,自成院落也相当安全。因在战时无力修缮,已颇老旧,既不白也非“宫”。在此住了八年的齐邦媛,也从未见过白塔在何方。

从乐山师范学院后门出来,到乐山文庙,有好几公里路程。
乐山文庙古称嘉定府文庙,始建于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乐山文庙作为武大校本部使用了八年之久,见证了抗战后方的烽火岁月。武汉大学西迁纪念展《烽火西迁路—武汉大学在乐山》位于文庙大成门。1938年至1946年,武汉大学前后有3000名学生来到乐山继续求学。展览讲述当时武汉大学师生冒着日军炮火,沿着长江逆流而上,一路西迁到乐山,不畏苦难、弦歌不辍、刻苦攻读的艰苦岁月。
齐邦媛所在的文法学院在文庙上课,总图书馆也在文庙。武大是迁校后方时带出最多图书的大学,也颇以此自傲。大学四年,上课的教材多由该班课代表借出书,分配给同学先抄若干再去上课,所以笔记本是必须的。
学生们通常是到嘉乐纸厂门市部去购买笔记本。
说到嘉乐纸厂,笔者并不陌生。因为笔者在《成都晚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李劼人与嘉乐纸厂》(见1984年4月25日《成都晚报》“锦水”副刊)。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笔者是学经济的,对经济史饶有兴趣。无意之中接触到写《死水微澜》那个作家李劼人兴办实业的资料,于是写了这篇短文。
而齐邦媛写嘉乐纸厂笔下生风:“由文庙门前月弭塘石阶左转上叮咚街,到府街、紫云街,要走许久才到嘉乐门大街找到嘉乐纸厂的门市部。进门第一眼所见,令我终生难忘,简直就是乐园中的乐园景……宽敞的平面柜上、环绕四壁的木格架上,摆满了各种雅洁封面的簿子,尺寸大小皆有,浅蓝、湖绿、粉蝶、鹅黄……,厚册并列,呈现出人生梦中所见的色彩!
那著名于大后方的嘉乐纸有千百种面貌,从书法珍藏的宣纸。到学生用的笔记簿都是艺术品,是由精巧的手,将峨嵋山系的竹木浸泡在流经嘉定乐山大佛脚下的岷江水制成。一位博物馆专家说,数百年后芳香仍在纸上。”

武大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系,淘汰率也最高。期末考试后不久,齐邦媛听一位同学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统考她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齐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在她的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她去昆明,转读西南联大外文系。身在乐山,心已飞往昆明,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同学都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过暑假了。而此时的她却面临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

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齐邦媛是幸运的。某天她接到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要她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怎会召见她这个一年级学生呢?接到通知,齐邦媛是惊骇多于荣幸。当地走进朱光潜在文庙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见到了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先生47岁,以齐邦媛那时的年纪眼中,所有超过40岁的人都是“老人”了)。朱对她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齐说她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高中毕业时,齐父和她的老师都希望她上中文系。朱又问了她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他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这最后一句话,决定了齐邦媛的后半生。
中央大学的孙先生对齐说,“朱光潜先生有篇《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是从文学教育者立场写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课,该是很幸运的事,何况他亲自劝你转系,还自愿担任你的导师,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发。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陈源(西滢)先生、袁昌英先生、陈寅烙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实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并不更强,而且也没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这种缘分。”
孙先生的分析使齐邦媛下定决心留在武大。说不出什么原因,也许那溯江数百里外的江城,对她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朱光潜的话也打动了齐邦媛,她终生以此为业,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又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推介至西方世界。
在文庙配殿那间小小的斗室之中,齐邦媛作为朱光潜的学生,听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课。朱先生讲书表情严肃,也很少有手势,但他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讲述雪莱的《西风颂》。朱先生说,中国自有白话文学以来,人人引诵雪莱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然而,雪莱的颂歌所要歌颂的是一种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灵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慑力量。全诗以五段十四行诗合成,七十行必须一气读完,天象的四季循环,人心内在的悸动,节节相扣才见浪漫诗思的宏伟感人力量。
朱先生教学生用the mind's eye想象西风怒吼的意象(imagery)。这是齐邦媛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尽。
1945年,极寒冷的二月早上,文庙坝星门旁石柱上贴了一大张毛笔布告,墨汁淋漓似乎未干:“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国巨型飞机一百七十四架B29轰炸机轰炸东京,市区成为火海,日本首相惶恐,入宫谢罪。”站在这布告前包括齐邦媛在内的数百个中国大学生,经历战争八年之后,大多数的人全靠政府公费生存;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在大石板铺的文庙正厅,读到这样的复仇消息,内心涌出复杂的欣喜。
这时,校长王星拱突然在文庙前广场召集师生,宣布一个重要的讯息:战事失利,日军有可能进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紧急时往安全地区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师管区司令部保护,在必要时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彝族自治区。同学们都已成年,不可惊慌,但必须有心理准备。同学们在大学很少见到校长,更少听他训话。齐邦媛记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风中,中国早期的化学学者、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校长穿着他的旧长袍,面容清瘦,语调悲戚,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这之后六十年,走过千山万水,“雷马屏峨”这四个字带着悲壮的声音一直在齐邦媛心中不时响起。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她活着的最大依靠。

2011年5月下旬,华西都市报记者电话联系到齐邦媛老先生。由于年事已高,近期身体又稍显虚弱,本来已不打算再接受媒体采访的齐邦媛,一听到华西都市报是来自四川的媒体,当即答应受访。她说:“我曾在四川生活八年,对四川这片土地的感情很深,很想念。”话语中,她对四川的怀念之情、眷眷之心溢于言表。
作者简介
蒋少龙,“老三届”和“新三届”学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杂志社编审,四川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农村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已退休。
来源:永远的华西
作者:蒋少龙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