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眉山与三苏的产生‖潘殊闲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眉山与三苏的产生
潘殊闲
三苏崛起于宋开国百年前后,并悉数从眉山走出,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乡土基因的角度言,可谓眉山孕育了三苏。这包括眉山的钟灵毓秀、眉山自唐以来的移民文化;眉山淳朴崇古的文风世俗;眉山浓郁的诗书文化氛围和文化家族风气;眉山苏氏家族的文化道德积累;眉山苏氏家族姻亲,特别是眉山程氏家族与苏氏家族的联姻,程夫人的贤惠、干练、知书识礼,培育、成就了三苏。
眉山的钟灵毓秀对三苏的沾溉
宋代眉山,以其文化隆胜,文人辈出而闪耀于世,这当中,最耀眼的当属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唐宋八大家宋人占六席,其中四川、江西各分占三席。而四川三席全部集中在眉山。换言之,眉山三苏父子占据唐宋八大家中宋代部分的半壁,占据整个八大家的三分之一强,这种现象不仅在唐宋两朝绝无仅有,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难有匹敌。

眉山向来不是中心城市,何以一朝一地一家集中拥有如此璀璨的文化巨星,它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眉山为古眉州治所。《舆地广记》对眉州有这样的解释:“眉州,秦属蜀郡,汉属犍为郡,晋宋皆因之。齐置齐通郡,梁及后周皆因之。隋开皇初,废齐通入眉山郡。唐武德二年,析嘉州置眉州。天宝元年,改为通义郡。后复为眉州。皇朝因之,统县四。”对眉山的历史沿革则如是说:“望,眉山县,本汉武阳县地,后分置齐通县,为齐通郡治。梁及后周皆因之。隋开皇初,郡废,改齐通曰广通。仁寿元年,改为通义。唐置眉州,皇朝太平兴国二年改为眉山。按西魏置眉州,隋置眉山郡,皆在今嘉州,其后州县之名迁于此耳。”
由上可知,眉州、眉山之名历史上屡有变迁。地名虽有迁变,但对于眉山这方江山形貌来说,则几乎未有太大变化。查阅相关资料可以看到,眉山自古就有“古之形胜地”的美誉,“山秀水清,通衢平直”(宋·祝穆《方舆胜览》),为“江山秀气所聚”(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学者独盛,以诗书为业,以名节相尚”(《方舆胜览》),位于成都西南约80千米处,介于岷山、峨眉山之间,有所谓“峨眉揖于前,象耳镇于后。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之誉(清雍正《四川通志》)。岷江纵贯全境。眉山境内,岷江之边,在一片稻田、果园和菜园中涌起一座浅丘蟆颐山,因状如蟆颐而得名。“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这是苏轼对家乡的由衷赞美。
眉山为成都平原的一颗闪亮的明珠,这里山清水秀,沃野千里,实乃风水宝地。大诗人陆游游览至此,不禁大发感叹:“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
可见,千古眉山渥岷江之丰润,撷峨眉之灵气,钟灵毓秀,物华天宝。古云“一方水土育一方人”,生长在这样的人间胜地,诞生人杰才俊,当是迟早的事。

客观地说,三苏的出现,与眉山天然形胜的自然环境有不小的关系。眉山有山有水,有宽阔平畴的田野,有密如蛛网的沟渠,“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膏腴之地,滋养了眉山人的大器,峨眉的俊秀孕育了眉山人的灵气,北宋立国以来的“百年承平”带来了眉山经济社会的富庶繁盛。在这种天地人和的环境里,三苏的出现,可谓正当时。
对自己家乡的胜景,三苏相当认同且赞不绝口,从中亦可以看到这种乡土基因的沾溉。苏轼对自己生长在长江上游颇多自豪:“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他对峨眉山下的眉山相当认同:“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我家岷蜀最高峰,梦里犹惊翠扫空。”在苏轼作品中,用“岷峨”代指家乡,几乎成为一种习惯,岷峨二山都在眉山周边,同时,岷亦有岷江之意,故对于远游的苏轼来说,它们都应是远望家乡、思念家乡、赞美家乡的代名词。查苏轼诗文集,以“岷峨”一词出现的作品有十多首,如“岷峨天一方,云月在我侧”“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在《眉州远景楼记》中,苏轼曾这样饱含深情地遐想:“若夫登临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轼将归老于故丘,布衣幅巾,从邦君于其上,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以颂黎侯之遗爱,尚未晚也。”
苏辙也有深厚的家乡情结,曾对回四川的老乡戴朝议说:“岷山招我早归来。”晚年时他曾颇多伤感地回忆道:“思家松菊荒三径,回首讴歌沸二天。”
苏洵对家乡也充满激情,有云:“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并声言:“古人居之富者众。”这种对家乡的认同与眷念,甚至可以从众多的“眉山苏轼”“眉山苏辙”的署名中得以窥见。

眉山的移民文化底蕴对三苏的滋养
四川在历史上自西汉文翁帅蜀开始,文教始兴,俗称“文翁化蜀”。在文翁化蜀的影响下,蜀中学术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司马相如、扬雄等有全国影响的文化名人, 以至“蜀学比于齐鲁”。诚如清雍正《四川通志》所云:“蜀虽僻处遐方,沐浴诗书之泽,熏陶礼乐之教,无不油然兴起。”
从汉迄唐,成都都是蜀文化的中心。在唐代,成都经济繁荣,社会发达,文化昌盛,享有“扬一益二”的美名。
而从唐、五代开始至宋,由中原向四川的移民运动,又大大推动了西蜀(特别是眉山)文化的兴旺发达。这次移民运动,大约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安史之乱”时期。在长安沦陷前期,唐玄宗带着大批人马逃到成都。随着战争的继续,入蜀的人数愈来愈多,大诗人杜甫即是其中一个。他诗中有“二十一家同入蜀”之语。
第二阶段是唐末黄巢起义期间,唐僖宗再度避蜀,大批文武大臣亦随之入川。
第三阶段为五代时,因中原战乱,素有“天府之国”的西蜀成为一方避乱乐土。
第四阶段为两宋之交。靖康之难,掀起一次北人徙蜀的高潮。
4次移民中,对宋代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三次,而在唐末五代移民中,眉州在四川各州中接纳移民最多。这些移民中较为著名的有眉山石氏、眉山孙氏、眉山家氏、眉山史氏、眉山程氏、眉山黄氏、彭山冯氏、彭山程氏、彭山师氏、青神陈氏、青神杜氏、青神史氏、青神贺氏、丹棱史氏、丹棱徐氏、丹棱杨氏(刘琳《唐宋之际北人迁蜀与四川文化的发展》)。
迁蜀的北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官宦世家,他们推崇的就是读书应试,因而,他们的加入,对推动眉山(眉州)的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唐末五代天下大乱的背景下,西蜀因为良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成为广大中原氏族大家的避风港。这带来南北文化的联姻交融,必然促使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自然的形胜,加人文气氛的营造,眉山已具备挑战文化名都成都的“资本”。事实上,宋代四川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确实还是北人迁蜀最集中的成都平原和眉州地区。苏氏家族虽谈不上是上述历程中迁蜀的移民,但也是从北方远道而来的官宦后人,置身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特殊的文化生态孕育了特殊的文化巨人。如唐末避难迁蜀的洪雅(眉州属县)田氏文化名人田锡,就对西蜀后人三苏产生了影响。田锡文论强调自然,有云:“禀于天而工拙者,性也;感于物而驰骛者,情也。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宋·田锡《贻宋小著书》)
这一观点被苏洵继承,并对田锡“微风动水”的比喻有进一步的发挥。他有一篇《仲兄字文甫说》,颇有代表性:“且兄尝见夫水之与风乎?油然而行,渊然而留,淳洄汪洋,满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风实起之。蓬蓬然而发乎大空,不终日而行乎四方,荡乎其无形,飘乎其远来,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风也,而水实形之。今夫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纡余委蛇,蜿蜒沦涟,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云,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徐而如徊,揖让旋辟,相顾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乱如雾,纷纭郁扰,百里若一,汩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磅礴汹涌,号怒相轧,交横绸缪,放乎空虚,掉乎无垠、横流逆折、濆旋倾侧,宛转胶戾,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鹭,跃者如鲤,殊状异态,而风水之极观备矣!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
虽是对其兄涣之名的臆解,而其思想却渊源有自。无独有偶,苏轼论文也受田锡影响,有云:“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这段话已成为中国文论史上的经典之论,而乡贤的影响与后人对乡贤的踵继于此观之可谓相当明显。父子一脉相承的文论思想不是偶然的,它至少说明,在三苏成长的道路上,眉山特有的移民文化氛围和文化成果对三苏的影响是客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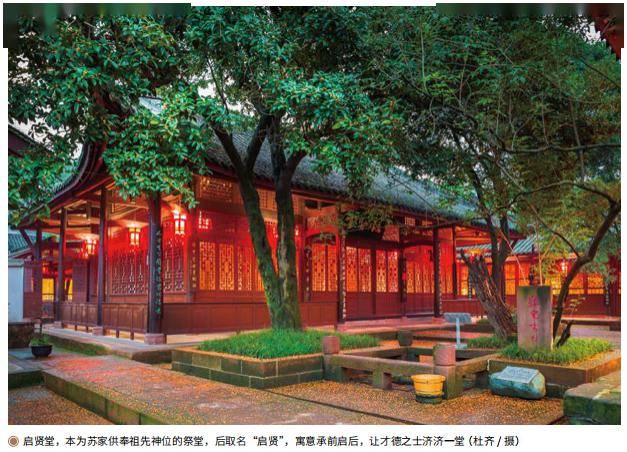
宋代眉山兴盛的教育科举对三苏的影响
宋代的教育机构,官办的有府学、州县学,民办的有私学及书院等。据宋赵与时《宾退录》卷1载:“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山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闻。”所谓“山学”,就是私学。在当时相当发达,生员不少。据胡昭曦《四川书院史》统计,宋代四川各地建有书院29所,其中眉州有5所,分别是:
东馆书院:在眉州城西75里东馆镇(今眉山市东坡区三苏镇),宋绍兴建(明·曹学佺《蜀中广记》)。
云庄书院:在眉州城南,眉州人史少弼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建(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北园书院:在眉州北郊,是曾知眉州的李埴于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以前建(《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巽岩书院:在眉州丹棱县治北15里,“宋绍兴间建”(《大清一统志》)。
栅头书院:在眉州丹棱县治南40里栅头镇,“宋绍兴间县令冯时行建”(《大清一统志》)。
其实,这是不完全统计,且都在三苏之后所建。在三苏时代,眉山的教育机构已相当发达,仅以三苏成长过程中有关文献所载,就有天庆观北极院,苏轼就学时,有童子几百人(苏轼《众妙堂记》),苏轼对自己的这段求学经历颇多美好回忆,如:“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长之。学日益,遂第进士制策,而太初乃为郡小吏。其后余谪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吴师道为汉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岁日,见师道求衣食钱物,且告别。持所得尽与市人贫者,反坐于戟门下,遂卒。师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骂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开目曰:不复烦汝。步自戟门,至金雁桥下,趺坐而逝。焚之,举城人见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陈道人也。’”(苏轼《东坡志林》)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为诗,诗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语,如‘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之句,皆可爱也。予幼时尝学于道士张简易观中。伯祥与简易往来,尝见予,叹曰:‘此郎君贵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苏轼《东坡志林》)
还有寿昌院等。《爱日斋丛抄》卷4载:“眉山刘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寿昌院,从游至百人。苏明允命东坡兄弟师之……坡兄弟应制科,微之赠诗有曰:‘惊人事业传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别无他祝,只愿双封万户侯。’自是三苏名著天下。”一个天庆观北极院,就有童子几百人,而一个寿昌院,从游者又有百人,由是观之,眉山之城,学习风气,堪称浓厚。
这种盛况,在苏轼的《谢范舍人书》一文中已有描述:西蜀在仁宗时代“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又说,“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释耒耜而执笔砚”,这是文化隆胜,尚读书的形象表述;而一年“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亦可以看到眉山人读书仕进的高比例。换言之,读书有理,读书有盼,读书改变人生命运已成为眉山人的坚定信念。“千载诗书城”的美名当源于众多眉山士人的“读书情结”。
蔚然成风的读书文化已成为眉山的一道亮丽风景。诚如宋祝穆《方舆胜览·眉州》在“事要”中引张刚《通义儒荣图序》所云:“后世以蜀学比齐鲁,而蜀之学者亦独盛于通义[注:通义为眉州治所。太平兴国元年(976)改通义县为眉山县]。政和御笔:‘西蜀惟眉州学者最多。’”又引《修谯楼记》:“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方舆胜览》引任熙明《教授题名记》云:“蜀为西南巨屏,由汉以来,号为多士,莫盛于眉、益二邦,而嘉定次之。”
“其民以诗书为业”,道出了宋代眉山人才辈出的“秘笈”。苏辙在《张恕寺丞益斋》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家亦多书,早岁尝窃叩。晨耕挂牛角,夜烛借邻牖。经年谢宾客,饥坐失昏昼。堆胸稍蟠屈,落笔逢左右。乐如听钧天,醉剧饮醇酎。”这种诗书生活是那样的富有魅力。家乡蔚然成风的读书记忆,带给苏辙永远的“享受”。
苏辙少年的读书生活当是眉山这座诗书城的读书人潮的缩影。俗云:有数量才有质量。正因为有大量的读书之人做基础,故“拔尖”人才便呼之欲出。这是小小的郡城眉州敢于比肩甚至赶超通都大邑成都的“诀窍”之一。
办书院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才,而读书求学的人,大都要参加科试,科举之盛,又成为眉山教育中的一大亮点。晁公遡在《今岁试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诗送之》中写道:“吾州俗近古,他邦那得如。饮食犹俎豆,佣贩皆诗书。今年属宾兴,诏下喧里闾。白袍五千人,崛起塞路衢。入门坐试席,正冠曳长裾。谈经慕康成,对策拟仲舒。吟诗必二《雅》,作赋规《三都》。传闻选主司,考阅须鸿儒。果然提权衡,未尝谬锱铢。得者固惊喜,失者亦欢呼。乡党为叹息,是事盖久无。老守蒙此声,增重西南隅。何以为子谢,举觞挽行车。少留尽一醉,归驾且勿驱。”
一州四县有五千人应试,教育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民国《眉山县志·选举志》,对两宋眉州登科进士作过统计,云:“眉州科第莫盛于宋。考旧志及雁塔碑所载,南北两朝中甲乙科者八百八十人。”这还不包括进士甲乙科以下,以及明经诸科等类。一个不起眼的小州在300年间有如此多的士子登科折桂,实在是了不起的现象。
而一句“佣贩皆诗书”,或许道出了其中的一些玄机。这句诗至少可作三解:
一是指全州书商书贩多,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书的需求多,销售市场大,当地读书蔚然成风,读书人蔚为大观。
二是眉山是全国的出版发行中心,书商书贩遍布全城,眉山的书籍市场异常火爆,已俨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中心城市。
三是即如佣贩这样卑不足道的市井之人,也是诗书的爱好者,这又从一个侧面证明全州人爱好学习,有文化的人所占比例不小,全社会已然形成一种学习的风气和氛围,换成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
的确,西蜀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人谓之“天府”。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加之特有的盆地地形,蜀人与外界联系不易,对外界的了解也较少,故多自足感。自文翁化蜀以来,蜀地教育日胜,“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但蜀人读书并不急于求官,而更多的是志在道德文化修养。
宋初的眉州,还发展出一种慕古求实的学风。眉州士人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对外面盛行的片面追求形式、轻薄浮艳的“时文”,颇不以为然,而外面的人则指责眉州人迂阔。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这说明,宋时眉山,完全是一个诗书礼仪之邦,民风崇古醇厚,文明诚信,遵纪守法,这些乡风民俗对三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三苏能够不苟于世俗,凛然而立,卓尔特行,令万世景仰,家乡的风俗熏陶与文化教育对其影响不可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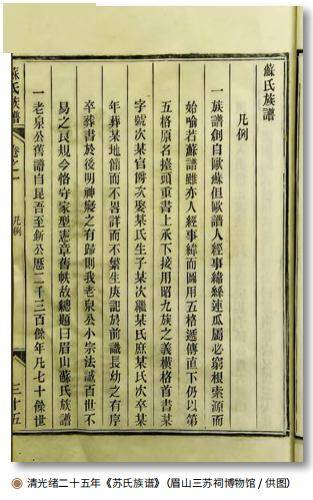
宋代眉山发达的出版传播业对三苏成长的帮助
由于眉州及西蜀教育发达,读书人多,因此,对书籍需求量大,这是眉山成为宋代著名三大刻书中心的重要原因。南宋初,晁公遡在《眉州州学藏书记》中说:“郡之富于文,不独诸生之言辞为然,盖文籍于是乎出,至布于其部,而溢于四方。”“布于其部,而溢于四方”,形象地描绘了眉山书籍出版传播之丰富和广远。而前面所引“佣贩皆诗书”亦可佐证眉山出版传播业的昌盛。
读书人多,刻书贩书人多,藏书人(楼)也多。宋代眉山著名的藏书楼有孙氏书楼。孙氏书楼初建于唐开成间,中有兴替,宋代并建有山学。由唐迄宋,书楼延续了数百年,人号“书楼孙家”(宋·曾巩《隆平记》),对传播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魏了翁有《眉山孙氏书楼记》,详细记载了书楼的沿革发展历史。宋祁守成都时,曾作《寄题眉州孙氏书楼》:“鲁简多年屋壁藏,始营翚棘瞰堂皇。髹厨四匝香防蠹,镂椠千题缥制囊。定与乡人评月旦,何妨婢子诵灵光。良辰更此邀请赏,庭树交阴隽味长。”
这种出版传播业的兴盛,对士人是一种良性的诱导,书香满城,书香醉人。在这样的诗书之城,文化的普及已走在全国的前列,而置身其中的莘莘学子,孕育大师,孵化名人,可以说已是水到渠成,势不可挡。
事实上,眉山苏氏家族也多得益于本地发达的出版传播业。如前所引,苏辙自己就曾说“我家亦多书”,苏轼也说他们家:“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看来,苏家确实多书。这大约有以下数端值得总结:
第一,苏家爱书。没有对书的钟爱,是不会着意收集收藏图书的。
第二,眉山作为出版传播中心,图书的购买相当容易,这也客观上给藏书提供了便捷。
第三,作为出版传播中心,眉山版的图书对眉山本地的消费者来说,少了不少运输等成本,购买相对便宜,这对并不富裕的苏家来说,满足其对文化的爱好较为容易,也可花小钱办大事,藏书成本得以大大降低。
正是由于眉山便捷便利的图书出版、传播、销售环境,使三苏在家乡能从容地徜徉在书海的世界。不仅如此,二苏从小还亲炙于父亲的教诲。苏洵曾潜心攻读经史百家之书,并亲自辑校数千卷书作为教材教育二子。倘若没有眉山成熟发达的图书市场,对于并不富裕的苏氏家族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三苏的成长道路上,眉山发达的出版传播业起到很好的催化作用。
宋代眉山的家族文化传统与三苏成长的文化生态
眉山的家族,在宋代,大抵可分为土著家族和移民家族两类。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两类家族相互融合,融合的纽带就是联姻。
读书仕进是他们共同的心声。宋代眉州彭山人吕陶曾说:“眉阳士人之盛甲两蜀,盖耆儒宿学,能以德行道义励风俗,训子孙,使人人有所宗仰而趋于善。故其后裔晚生,循率风范,求为君子,以至承家从仕,誉望有立者众。”(《朝请郎新知嘉州家府君墓志铭》)元代仁寿人虞集也说:“昔者吾蜀文献之懿,故家大族子孙之盛,自唐历五季至宋,大者著国史,次者州郡有载记,士大夫有文章可传,有见闻可征。所谓贵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虽贵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盖犹有九品中正遗风,谱牒之旧法,不独眉俗为然也。”(《题晋阳罗氏族谱图》)
宋代成都人范镇曾说:“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那么,打破这种局面的,无疑首先是南迁移民。南迁移民,既已丧失政治权力,经济上亦无更多优势可言,唯一可以操纵的就是文化“发家”,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可行的生存发展模式。
眉山苏氏家族是来自于北方的南迁移民家族,虽“阅五季皆不出仕”,至苏涣才始有仕进,但眉山苏氏家族文化传家的根柢与眉山特有的崇学尚文的风俗,不谋而合,这种点与面的交融,共同促进了眉山家族文化传统的长期兴盛。
与这种家族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是颇有眉山地域特色的等级“江乡”婚。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说:“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这种婚配习俗是过去门阀士族制的一种孑遗。
以眉山苏氏家族为例,据苏洵《苏氏家谱》所载,眉山苏氏的始迁祖是唐代宰相苏味道。苏味道,赵州栾城人,“延载中,以凤阁舍人检校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岁余为真……张易之败,坐党附,贬眉州刺史。复还益州长史,未就道卒。”(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苏味道有一子在眉州定居下来,从此眉州始有苏姓。历经唐末五代,眉山苏氏逐渐衰落,年谱失修,以至苏洵作《苏氏家谱》时只能“上至于吾之高祖,下至于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不过从眉山苏氏族源看,仍应属于眉州大家旧族。五代宋初,与这样一个大家旧族通婚的有眉州黄氏、李氏、史氏、石氏、杨氏等地方大家,他们也基本上是从中原迁往眉山的士族,可谓门当户对。
这种联姻,确保了士族家庭的文化血脉不易中断,对后代的文化修养、道德素质有基本的保证,故这种家族产生政治与文化名人的概率高于一般家族。
宋代眉山苏氏家族与三苏成长的家学渊源
眉山苏氏直接发源于唐代凤阁侍郎苏味道。神龙(周朝武则天与唐中宗李显年号)初年,苏味道坐张易之党附,贬眉州刺史,不久又迁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苏氏(苏洵《家谱后录上篇》)。但由于五代战乱等多重原因,至苏洵修家谱时,谱系已有些模糊不清,所以,苏洵说:“自益州长史至吾之高祖,其间世次皆不可纪。而洵始为《族谱》以纪其族属,《谱》之所记,上至于吾之高祖,下至于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呜呼!高祖之上不可详矣。”
苏洵之上三代分别是:高祖苏祜、高祖母李氏;祖父苏杲、祖母宋氏;父苏序、母史氏。对于自己的先辈,苏洵曾在《族谱后录下篇》有详细描绘和评述。
由苏洵的叙述,可以见出上述三苏先人有以下一些共性:乐善好施,淡泊名利;忠敬笃孝,重义行侠;无心仕进,随遇而安;外家多才,贤为辅佐。
对于无心仕进,苏洵有一段解释:“洵闻之,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及其后,僭伪之国相继亡灭,圣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是以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及其教化洋溢,风俗变改,然后深山穷谷之中,向日之子孙,乃始振迅相与从官于朝。”(苏洵《家谱后录上篇》)苏辙也有解释:“苏氏自唐始家于眉,阅五季皆不出仕。盖非独苏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孙君堪始以进士举,未显而亡,士犹安其故,莫利进取。”(苏辙《伯父墓表》)
的确,苏氏先祖无心仕进,有其客观原因。苏祜、苏杲所在的五代,正当王氏、孟氏小朝廷,政治腐败,民生凋敝,蜀地的高才贤士耻与之为伍,只有“年少轻锐之士”才仕。入宋之后,蜀地动乱不宁,那种不仕于天下的父祖之训还有一种惯性的影响力,所以,苏序也未仕。
尽管三苏先人三代未仕,但因其具有良好的品性操守,却也是闻名乡里的贤达,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乐善好施、重义行侠、忠敬笃孝、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品性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三苏的人生仕履看,这种家族的精神品质,可谓一脉相承。特别是苏序,尽管年轻时不好读书,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却颇有识见。苏轼曾这样慨叹自己的先辈:“先君昔未仕,杜门皇祐初。道德无贫贱,风采照乡闾。何尝踈小人,小人自阔踈。出门无所诣,老史在郊墟。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 ”(《答任师中、家汉公》)置身这样的书香环境,耳濡目染,一种文化的苏醒与勃发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前所述,历经五代、宋初连年战乱,西蜀百姓苦于水深火热的日子,无心读书求学,又安土重迁,不愿外出为官。这种风气使得眉山在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之前,几乎无人参加科举,而率先打破这种封闭的不肯向学以及学而不仕传统的,就是苏序这位一度不好读书的豪侠之士。
苏序晚年颇有诗书情韵,“晚乃为诗,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皆见于诗”,诗虽不工,但却是一个“表里洞达”的“豁然伟人”。这对其三个儿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三个儿子都参加了科举。长子苏澹举文学进士,因学业未精,未中,又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早亡,未有所成。二子苏涣于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乙科及第。三子苏洵虽“壮犹不知书”,但苏序并不强之,且对人说“是非忧其不学者也”。既而苏洵果然奋发力学,尽管屡次考试未中,却最终成为文章大家,且培养出驰骋文坛的苏轼、苏辙兄弟,并与其子以文学名天下,为学者所宗。
苏序生前虽没有入仕,只是因为儿子苏涣中举做官,才被赠尚书职方员外郎。从直接的层面说,苏序在政治、文学上都谈不上什么影响和成就,但他对眉山苏氏家族以教育起家、崛起于寒微,为逐渐形成文学世家、士大夫望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苏序的豪迈性格及过人才气,为后代所传承,也被子孙所称扬。比如,在祖父去世多年之后,苏轼曾向学生们谈起祖父,说:“祖父名序,甚英伟,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宋·李廌《师友谈记》)可以这样说,苏序修身行义,未显于国却显于乡党。他乘时得志,不在己身而在儿孙。宋人应俊在《琴堂谕俗编》中曾做过这样的述评:“余尝闻眉山苏仲先序,为人疏达,轻利好施,救人之急,孜孜若不及。及岁凶,卖田以赈其邻里乡党。至冬间丰熟,人将偿之,公辞不受,由是破散其祖业,迫于饥寒,然公未尝以为悔,而好施愈甚。遇人无疏密,一与之倾心焉。或欺而侮之,公亦不变色。人莫测其用心。后生子曰洵老泉先生,孙曰轼东坡先生,曰辙颖滨先生,皆显名天下,人以为善恤乡邻之报。”
这样讲,似不无道理。事实上,因为苏序的“行善积德”,自苏序后,眉山苏氏家族文星闪耀,轩冕相继,成为震古烁今的文化大家族,其中的因由,不能不让人对这位苏氏家族的先辈、三苏的父祖辈油然生敬。
其实,苏涣金榜题名,并仕至高官,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苏氏家族,他对眉山乃至西蜀都是一件大事,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苏辙描写当时的盛况是“乡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绝”。而曾巩在《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中则这样写道:“蜀自五代之乱,学者衰少,又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仕。君(苏序)独教其子涣受学,所以成就之者甚备。至涣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受学,及其后,眉之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
苏轼在《谢范舍人书》中也有这样的感叹:“尝闻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年间,学校衰息。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途。其后执事与诸公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刘,又以远过。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则其他可知矣。”
可见,苏涣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不仅打破了苏氏三代不仕的局面,且为乡里开辟出由科举而仕宦的康庄大道。而苏涣为政的清廉干练,还为苏氏子弟树立了从政的榜样。苏轼、苏辙都对伯父充满敬意,苏辙在其《伯父墓表》中说:“苏氏自唐始家于眉,阅五季皆不出仕。盖非独苏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孙君堪始以进士举,未显而亡,士犹安其故,莫利进取。公于是时独勤奋问学,既冠,中进士乙科。及其为吏,能据法以左右民,所至号称循良。一乡之人欣而慕之,学者自是相继辈出。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常千数百人,皆以公为称首……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好读书,老而不衰。平居不治产业,既没,无以葬。善为诗,得千余篇……其为吏,长于律令,而以仁爱为主,故所至必治, 一时称为吏师……辙幼与兄轼皆侍伯父,闻其言曰:‘予少而读书,师不烦。少长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游于途,行中规矩。入居室,无惰容。非独吾尔也,凡与吾游者举然。不然,辄为乡所摈曰:是何名为儒?故当是时,学者虽寡,而不闻有过行。自吾之东,今将三十年,归视吾里,弦歌之声相闻,儒服者于他州为多,善矣。尔曹才不逮人,姑亦师吾之寡过焉可也。’皆再拜曰:‘谨受教。’”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二苏回乡奔母丧服满,回到京师,拜访了伯父苏涣,向其请教为政之方。伯父告诉他如场屋中作文:“有事入来,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了而后行,无有错也。”此言已成为苏氏“家法”。从苏轼、苏辙一生的仕履看,伯父的影响显而易见。比如,伯父“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好读书,老而不衰”“长于律令,而以仁爱为主,故所至必治”等,二苏都完全继承;甚至伯父“平居不治产业”,也对二苏有影响。
苏轼对钱财看得甚淡,曾自称“素来不善治生,禄赐所得,随手耗尽,道路之费,囊橐已空”。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不仅居无定所,且所置少量田产也无力经营。苏轼曾有这样的感叹:“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访问,终不可得。岂吾道方艰难,无适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虽一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相传苏轼晚年自海南北归,在阳羡倾囊购得一宅,后因生怜惜之情而将房屋退给原房主,并焚毁屋券,不索其直,最后竟客死于借居(宋·费兖《梁溪漫志》)。苏轼去世后,几个儿子携家带口到颍昌依附苏辙,生事萧然,日子过得不轻松。从二苏仕履的特点看,苏涣的影响无处不在,确可谓“家有吏师遗躅在”。诚如元人王沂所评:“眉山苏氏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
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婚配对三苏成长的贡献
“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于闺门。”从苏洵《族谱后录下篇》可知,眉山苏氏自苏釿而下,生平记载稍详。剖析眉山苏氏婚配(本文只统计苏洵以上五代),对认识三苏的出现与崛起,颇有意义。
苏釿之妻——黄氏。文献记载简略,不知其详,据专载蜀中轶事的《茅亭客话》所记,黄氏“家习正声,自唐以来,待诏金门,父随僖宗入蜀”,说明黄氏系唐僖宗时入蜀的北方望族,亦为眉山之移民。
苏祜之妻——李氏。为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后,世曰瑜,为遂州长江尉,失官,家于眉之丹棱。李氏严毅,居家肃然,多才略,犹有窦太后、柴氏主之遗烈。
苏杲之妻——宋氏。事上甚孝谨,而御下甚严,善治生,有余财。
苏序之妻——史氏。史氏为眉之大家,“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俨从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将二十世。宋世号名族”(元·袁桷《史母程氏传》)。苏、史两家是世姻,后来苏辙亦娶史氏。苏序之妻史氏生性慈仁宽厚,生子三人,长曰澹,次曰涣,季曰洵。婆婆宋氏甚严,史夫人常能得其欢,以和族人。
苏洵之妻——程氏。苏、程联姻是眉山苏氏家族的一个转折点。程氏是眉山的名门望族,“其先武昌人,唐广明中讳琦者从僖宗入蜀,遂家于眉州”(晁公遡《程邛州墓志铭》),后来成为新兴的科宦之家。程夫人之祖、苏轼之外曾祖程仁霸,曾摄录事参军,程氏夫人之父程文应,为大理寺丞;程夫人之兄程浚与苏涣同举进士,程夫人之侄程之才(字正辅)、程之元(字德儒)、程之邵(字懿叔)都仕宦有声。可见,程家确实在眉山堪称大家望族。
苏轼晚年在惠州曾作《外曾祖程公逸事》,称外曾祖程仁霸“以仁厚信于乡里”,曾因仗义执言,而惊动天公地府,许以“子孙寿禄,朱紫满门”,最后“沐浴衣冠,就寝而卒”。苏轼自豪地总结说:“已而外祖父寿九十,舅氏始贵显,寿八十五,曾孙皆仕有声,同时为监司者三人,玄孙宦学益盛。”
程氏虽为外家,但从其先人的积德看,苏轼、苏辙的出现,亦不能说没有因果。
对苏氏家族来说,程夫人是苏氏家族见诸记载的第一位知书达理的才女,在苏氏家族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程夫人出生在那样的家庭,本身受过良好教育,“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她不仅为苏氏家族生养了苏轼、苏辙两个有出息的儿郎,带来了家族的繁盛,而且她还以一双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帮助丈夫卸掉治家治生的烦恼使其得以安心向学,使丈夫27岁之后尚能发愤图强而终成大名。在相夫的同时,程夫人不忘教育孩子。司马光在《苏主簿夫人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府君(指苏洵)年二十七犹不学,一旦慨然谓夫人曰:‘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府君由是得专志于学,卒成大儒。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励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进士第,又同登贤良方正科目。宋兴以来,唯故资政殿大学士吴公育与轼制策入三等,辙所对语,尤切直惊人,繇夫人素勖之也…… 呜呼!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虑高绝,能如是乎?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于闺门,今于夫人,益见古人之可信也。”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程夫人是成就三苏的关键性人物。没有她的理解与支持,没有她勇于治生持家,苏洵不可能27岁还能一心向学,成就自己的事业;而没有苏洵的觉悟和结识京城名流,二苏可能还困在眉山,没有这么幸运地认识那些赏识、提携他们的伯乐,也不可能这么早就扬名京城,为日后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对于自己事业与家庭的矛盾,苏洵在决意携子游京之后曾有这样的感叹:“一门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数口。为行者计,则害居者;为居者计,则不能行。恓恓焉无所告诉。夫以负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奋身而往,尚不可御……今也望数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缩而不进,洵亦羞见朋友。”(苏洵《上张侍郎第一书》)
关于程夫人对苏轼的培养,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公(苏轼)生十年,而先君(苏洵)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少年时代母亲所给予的这种名节教育,在苏轼的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可以从苏轼一生“微官敢有济时心”的伟大抱负和“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的人生实践中看到母亲程夫人的教育之果。正如《宋史·苏轼传》所云:“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
程夫人因为助夫教子,颇有成就,《大清一统志》将其列为眉州“烈女”。
要之,三苏崛起于宋开国百年前后,三苏悉数从眉山走出,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潘殊闲(西华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