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易旭东现象:发布华夏文明中“四川新闻”的学者型作家‖冯俊龙
易旭东现象
发布华夏文明中“四川新闻”的学者型作家
冯俊龙
还沉浸在易旭东《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上下册,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描摹勾画的“成都前世今生”画卷里,忽然接到这位难得见面的文友加朋友的信息,又推出了《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同样是上下册(上册《亚欧大陆无疆》,下册《巴蜀相向而行》,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同样又是皇皇数十万字。恭喜祝贺的同时,更加震惊易旭东从新闻工作的资深媒体人,到如今华丽转身成为学者型作家;从时政新闻、民生报道,到历史考古、地方志研究,跨越历史、文学、哲学、社科、经济等学科,成为集研究、写作于一身的学者型作家。其转型速度之快,转折之猛,成就之大,令人惊奇。“易旭东现象”,在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和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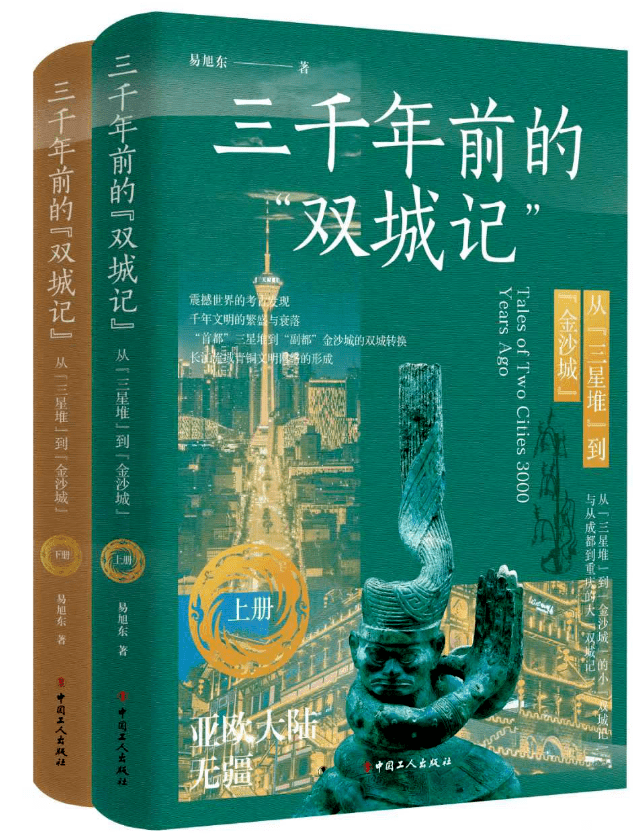
从发布时事新闻到发掘“古蜀旧闻”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从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开始试着寻找、破译易旭东为什么能从发布时政新闻到挖掘“古蜀旧闻”,从资深记者到纪实作家,从在报刊发表文章到著书立说,从报刊总编到学者作家背后的“秘密”。
看似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相逢知己却滔滔不绝、口才了得的易旭东,如今头衔不少,除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外,还有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特聘资深研究员、搜狐酒业发展研究院专家、天府文化学者、北宋人物史研究学者。如今,更是“巴蜀文化使者”“地志运用创新者”。在国内外报刊发表纪实作品650万字,50多篇作品获各种奖项,30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权威文摘报刊选用,选集出版,收入文库;继《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后,再推出姊妹篇《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可谓“三星堆学”“金沙城学”等古蜀文化的权威研究专家,打造出了“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融合的巅峰之作。
“三星堆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在本世纪初掀起高潮。其时,仅在成都、德阳,相关方面的学者、作家就多达200余人。但随着热潮渐退,特别是很多人以为“完成”任务,“工作结束”,选择“顺势退出”,人数锐减到不到20人。
易旭东是首批采访、组织报道三星堆遗址的媒体记者,亲眼目睹华夏文明代表之一的“三星堆遗址”(包括“金沙城遗址”),渐次在“误说”“歪说”兴起中,沦为“非主流研究”。他心有不甘,“逆流”而上,不管不顾,像一头忍辱负重的“倔骡”,一头扎进“三星堆学”“金沙城学”的研究之中,“度是寂寞日,做是清冷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努力发掘古蜀“旧闻”,一待就是十年之久。
皇天不负苦心人,易旭东终于从发布时事新闻的记者,完美蝶变,成为发掘华夏文明中“四川新闻”“成都故事”的重要发布者。一名长袖善舞的大特写记者,成为埋头苦干的学者型作家,转变为什么有这么大?特别是一个功成名就、人生过半的“爆烟子老头”(四川话:中年油腻男人),为什么要从门庭若市的高朋满座,心甘情愿去当“城市农民”,坐几乎与世隔绝的“冷板凳”?
这从易旭东的文字作品里可以看出端倪。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系统再现了3000多年前,成都平原上古蜀“首都”三星堆的湮灭、“副都”金沙城的崛起;“金沙城”作为“新”首都,增添了无数“中国故事”中的“成都创造”;上古时期的成都平原,逐渐与川东山地文化融合,形成巴蜀文化;良渚、宝墩村、巫盐古道、盘龙城文化与以三星堆、金沙城文化,在华夏大地交相辉映;成都、重庆与武汉、杭州,分别崛起于中国东西部,博大精深的长江文明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
在《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的姊妹篇《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中,易旭东通过“海阔天空的历史散打”“古今中外的地理图谱”“畅谈人性的哲学著作”“记载人文的风尚华章”这样的样态,阐释了古蜀文明源起、发展、延续,记叙了“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的内涵、豁达、美丽。成都不但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宜居城市,而且还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易旭东以他做新闻记者的敏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影视作品中,不断发现史志题材被戏说、假说甚至乱说。为了“对历史负责任的担当”,决定心无旁骛地坐几年甚至二十年“冷板凳”,利用十年时间乃至余生,对古蜀文化追踪溯源,对华夏文明在世界的地位进行梳理,做出一件足以令自己自豪、使后世称道的“大事”。
“要么不做,要做就力争做到最好”。易旭东与人迥异的性格,使他开始以作学者的严谨、深沉,从史籍、出土文物着手,专注田野考古,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民族特征、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和现场考勘。他从考古现场、文献史志中反复揣摩,精研细读勘证之后,再举以作家之笔挥毫,再现历史原貌,达到传播历史背后的故事、让读者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银河。
坚持不懈,终于“摘得属于自己推群独步的成果”。他站在新的起点上,不仅完成自己人生的华美转变,而且让华夏文明中的“四川新闻”“成都故事”,成为在文化强省的新时代奋进中的“史志背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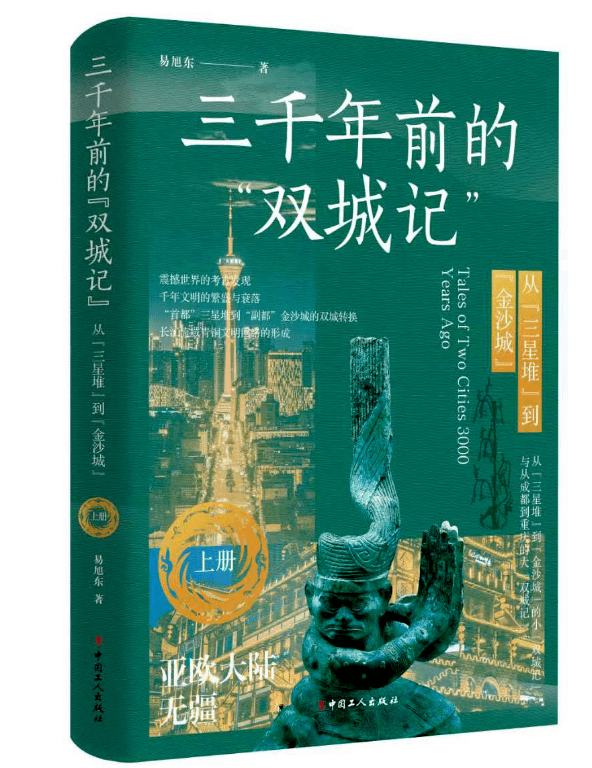
公园城市播报华夏文明的“四川新闻”
人类文明从古到今,不断推陈出新。今天的人们回首过去,从远古文明中寻找发生历史的成因,不时发现掩盖在时光深处的盛大辉煌,更是常常揭开被故纸堆隐藏的惊天秘密。易旭东在成都这座“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不时播报出华夏文明中的“四川新闻”,向世界传达古蜀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时刻刷新被古老岁月蒙住的重大发现。
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一种文明的地位,应该考证它的文明成果。
古埃及金字塔的巨石阵,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古印度的数字和佛教,古中国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的“四大发明”,遗迹尚存,至今影响人类。人类通过音乐、美术、雕塑、科技、宗教、文学等传承下来的思想,推进历史的作用更不可小觑。
自古以来,华夏文明对中国周边地区影响深远,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具有内陆文化特征的黄河文化、产生海洋文化特征的长江文化,将儒、释、道多元并存的学术思想,向世界广泛传播。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逐渐浸润地球村的每个角落。“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胸怀博大、包容并蓄,是中华文化的坚定自信。
易旭东在《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上册《亚欧大陆无疆》中,揭开了三星堆、金沙城作为中国西南文明中心的面纱。
距今5000年,在天府四川存续了3000年以上的古蜀文化,典型的代表就是今天发掘出来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能够证明这些文明曾经发生的依据,是大量文物、遗迹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古蜀国成为世界朝圣中心,使这里具有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古蜀地经常举行宏大、神圣的祭祀活动,吸引了远近众多的民族前来观瞻,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
人类对天地合一的神往,演绎成敬畏,“神”便诞生,成为人敬畏而祭祀的对象;后来,死去的人,因其不能消亡的思想,也成为可以控制人类欲望的对象,“魂”又被创造出来。易旭东根据在三星堆、金沙古城遗址出土的祭祀用品,以“燎祭”为题,播报了发生在古蜀地盛大而庄严的祭祀场景。在这些“旧闻”中,受祭的“神”“魂”,收受的祭品要焚烧成灰烬,不能焚烧的东西,也要摔碎。信仰便在盛大庄严的祭祀中产生、发展、传承。
今天的读者很难想象,3000年前闭塞蛮荒、交通不便,处于内陆的成都平原,居然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顶礼膜拜。他们携带大量的象牙等珍贵物品,从遥远的欧亚大陆、中南半岛跋涉而来,与古蜀人进行交换,虔诚地瞻仰戴着黄金面具的祭司。古蜀国的经济繁荣,已经盛况空前,成为引领世界前行的潮流。
3000年后,生活在金沙遗址、十二桥文化遗址附近成都市区的“成都街娃”易旭东,从承载着历史记忆的一幅画、一首诗、一块碎片,甚至一个不经意的传说中,深入挖掘,将掩埋在时光深处的“历史旧闻”,演绎出华夏文明中的“四川新闻”。远古蜀国,成为古人世界的“诗和远方”;古蜀文化,极大拓展了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
易旭东掀开以营盘山文化为源头,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成都商业街船棺与独木棺墓葬为代表的战国青铜文化的面罩,揭开它的神秘、模糊、朦胧、懵懂,再现了古蜀文明的伟大。他用“当局者”的角度感受,以“旁观者”的视野记叙,用记者的敏锐眼光,用文学的表现手法,纵横捭阖、引经据典,详尽阐述远古时候的长江、黄河造就与世界平行的巴蜀青铜文明。巴蜀文明早就与华夏文明融合,巴蜀人民的智慧早就造福人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讲话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正所谓‘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正是这种“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的“中国自信”,易旭东拂去时光尘土,在岁月深处不停打捞、发掘,不时提炼、总结出华夏文明不断演变中的诞生的“成都故事”,用文字的力量,把“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努力向外延展,让成都走向世界,让世界拥抱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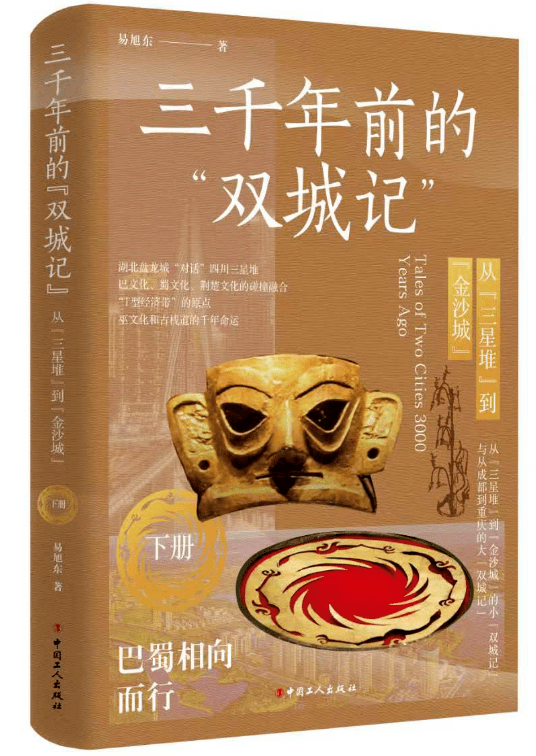
“中国经济第四极”的“现代双城”
习近平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易旭东自觉担负文化使命,创新性探源地方文化,立足巴蜀大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深耕史志,专注田野考察,精研天府文化,为成都这座“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修志立传,再从三千年前的“小双城”三星堆和金沙城,无缝对接到今天的“大双城”成都与重庆,将“中国经济第四极”的“双城”概念,扩大到世界范畴,为今日成都、四川乃至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发展,作出了有益探索。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比前部作品《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更进一步从文化源头深入细致地解密成都这座“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从人性角度,更具有深度和广度地阐释了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与世界文明的互动和交融,对世界的深刻影响,对今天成都、四川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作用不可忽视。如果说《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是揭开巴蜀密码的历史、人文、地理的文学词典,那么《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就是解说巴蜀文化与中华文化密切关系的历史阐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巴蜀文化从“巴文化”“蜀文化”的诞生、发展、传承,到二者之间的契合、发展,对助推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地位举足重轻。
《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下册《巴蜀相向而行》,易旭东通过“巫盐古道”,细叙古巴人发现食盐,更进一步加深对水的崇拜。人类文明的演变,可以说是对水的征服利用过程。原始文明对水的依赖,农耕文明对水的利用,工业文明对水的开发,无不是生命对水的依托,利用水改变自身命运,对外进行广泛交流,巴蜀文化得以与中原文化进行媾和,进而对世界文明产生影响。
恩格斯曾说过:“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通过他所做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古巴蜀人可以逐渐利用、支配自然界,但不可能完全掌控自然界。不能掌控是因为无知,无知即会产生恐惧,消除恐惧就会产生敬畏。
让今人深感震惊和意外,古巴蜀人的生活质量、拥有的文创力、艺术想象力、鉴赏力、遭遇的灾难程度,都远远超过今天人们的想象。
“天下之中”,远在3000年前,三星堆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三星堆文物具有世界影响力,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与“元典时代”的中国同步,确定东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思想世界的许多核心知识正在逐渐形成,政教样式的诗、书、礼、乐、易等,被后世儒家奉为经典。古成都人的精神世界已达到某种神秘高度。三星堆和金沙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为考勘中国文明历史演进途径开辟了新的路径。易旭东埋头苦读史籍经典、专心一意精钻传统文化,然后将所得成果转换为文字纪录片,不但为城市发展摇旗呐喊,而且赓续民族文明、区域文化,功莫大焉。
从“三星堆”到“金沙城”,形成成都平原的小“双城记”;再从成都迈步到重庆,形成中国西部的大“双城记”;最终是中国与世界平行、领先世界的强力支撑。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不断把创新的文明体系奉献给世界。
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中,向四周喷射出十二道光芒的太阳,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象征着光明、生命和永恒。四只展翅的神鸟围绕着太阳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地飞翔,寓意深远。三千年前的“双城”概念,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易旭东的《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对现代的“双城记”提供了不少营养。
源远流长的巴蜀文明收藏着中华文明的源代码。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板块上,成渝地区一直举足轻重,纵向从2020年成渝城市群要基本建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优良、生态环境优美的国家级城市群,到2030年成渝城市群完成由国家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的历史性跨越;横向要将成渝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城市群并列。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成都、重庆与武汉、杭州的文化互动、影响、传承,依托长江水路航道、大蜀道更加频繁。易旭东说:“荆楚文化、中原文化……顺着江流河谷、岭壑栈道,先后汇入四川盆地,与巴蜀固有的文化交融、碰撞,共同在封闭的地势环境中,‘逆反’地呈现出文化多元、立体荟萃的景象。”今天的成渝地区大力发展首店经济、首创经济、首发经济、首品经济,打造服务双城高频交流的“成渝第一商圈”,大力筑牢成渝双城首位城区、向美而生公园城区、都市产业示范城区、安居乐业首善城区、营商环境样板城区,成都这座“雪山下的公园城市”,自然就能让更多人充满信心,憧憬美好未来。
“易旭东现象”与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易旭东从研究型记者到学者型作家的演变,是踏实苦干、求真务实的“记者精神”的延续,也是潜心钻研、严谨治学的“学者风范”的再现。他极具洞察力、悟性,亦有良好的归纳提炼能力与持续学习能力,再加天生具有的通感能力,青年时期创作小说与刊发学术论文的功底,善于思考又使他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无时无刻都可以生发出破釜沉舟的勇气;一生从文的历练,仿佛拥有一副可以伸展到任何时代的“望远镜”,始终能够解析种种历史谜团,随心所欲地将学术成果“通俗化”、远古历史“现代化”。在得到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成都市金牛区作家协会等单位的认可和支持下,一套套论说巴蜀历史、追寻古蜀文化源宗的著作,接连横空出世。
易旭东有新闻人的敏锐和清醒,同时具备作家的敏感与自信,更令人欣喜的是,还蕴藏学者的严谨及自律。从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易旭东把历史嚼碎,再重新组合,“将史志与文学融合、文物与艺术联动、文化区块链与产业供应链互助”,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打破常规的“混乱”。其结果是,部分读者“读不懂”他的作品。
“读不懂”易旭东的书,也是“易旭东现象”之一。
让人惊讶的是,易旭东轻描淡写地说,有的人“读不懂”他的书,正是他“想要的目的”,自己解释部分读者“读不懂”他的作品的原因:他要“正本清源,守正创新”。那些“‘容易读懂’(的历史作品)不是记叙历史的标准”,就是要“故意”让一些人“读不懂”。只有“读不懂”,才晓得作者“写得烧脑”,才能“让你感到读史志读得‘恼火’”,这样才有动力“激发、搞热”你的脑子,促使你“压迫性的思考”。“思考,也是一种能量”。
史志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弄清历史发生的具体经过和原因。
易旭东说他的创作是“一项前沿性的跨学科史学研究”。他“与以往的历史学家、文化学者不同,除了需要调动视觉器官外,还要调动视、听、嗅、尝等其他器官,全方位接近和感知所研究的范围,也不满足于阅读史料文献,还要从出土文物甚至地志、民俗、传说中,寻找历史文化的蛛丝马迹,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将史志与文学融合,努力向文学世界的前沿靠近,向未知的深处开拓一下”。正是有了这样严格而独特的自我要求,在闭门谢客、潜心深研之后,创作出了史料稳准、行文畅美,观念独到、以古论今的鸿篇巨著。
阅读易旭东的作品,的确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外,还要不时“脑补”,查阅各种资料,对不懂甚至陌生的知识,进行了解、补充。他语言、句型的独特,思维的跳跃,知识的广博,已远远超出很多人的接受能力。他的作品,绝大部分还是如“新闻特写”一样,一读便懂;有一部分,必须进行深入思考。
这也许又是另外一种“易旭东现象”吧。
“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也是今天所有文学工作者创作历史文学作品的标杆。
易旭东已经走在前头。这位年过六旬、挺进古蜀文化研究的学者型作家,不忘初心,坚持创作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人、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历史”的“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想不到一直保持“街娃”调侃心态、“爆烟子老头”年龄阶段、“倔骡子”脾气性格、学者的翩翩风度、诗人的飞扬激情,60岁当30岁用,像混界百搭的高手,又走上考研、写作《大蜀道》(又同样是上下册)的路上……
真诚地祝愿易旭东创作出更多更优质的史志题材作品,在“史志旧闻”中挖掘出更多更有价值的“巴蜀新闻”“成都故事”,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增添更多辉煌,为让世界拥抱巴蜀、赞美成都激发“共情”作出更多贡献。
作者简介
冯俊龙,男,汉族,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协会会员。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四川日报》《巴蜀史志》《文史天地》《同舟共进》《党史博采》等报刊,人民网、中国军网、中国作家网等网站发表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中外文摘》及新华网、封面新闻、搜狐、网易、澎湃新闻等转载(摘)。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冯俊龙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