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难忘的延安岁月‖王兆相
难忘的延安岁月
王兆相
1938年初至1940年末,我在延安先后进过两期抗日军政大学。首先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高级班插班学习,后又到瓦窑堡抗大第四期红军干部支队学习。抗大毕业后,又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在延安学习、生活了两年半左右时间。通过学习,我在文化上、军事素质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而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了许多中央首长,直接得到他们的帮助教育。他们的言传身教和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毛主席对我学习生活上诚挚深切的关怀,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一、诚挚的关怀
1938年2月,我与张达志、孙超群带领警备六团在八路军总部和120师领导下,驻守晋西北偏关、清水河、平鲁、五寨一带,负责发动群众,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的进攻。当时是国共合作的抗日初期,根据地内形势有一定好转。经我向总部提出,总部同意我到延安学习。
我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先去见了滕代远总参谋长。他问我在进抗大以前,是不是先见见毛主席。我忙说:“那当然,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能见到毛主席了。”记得从晋西北120师师部出发前,贺老总还托我到延安后一定向毛主席转达他的几句话。我当时想,毛主席每天日理万机,处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那么多党、政、军大事,哪有时间来接见我呢。现在滕代远总参谋长提出来,那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了。他说:“那好,你先在招待所住下等两天,我与毛主席联系后再通知你”。
随后,我又去拜访了留守兵团萧劲光司令员,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向他们汇报了警备六团在晋西北的防务情况,也谈了一些神府佳榆情况。
在如何与毛主席见面这件事上,我在招待所住下后想了很多,怎么见、见了汇报哪些事,主席可能问我些什么问题。我在招待所也听前线回来的同志讲:有一个从前线回来的团长在主席接见他时,首先把名片递给主席,而后再报告他是某某团团长。主席对这一套递名片、报官职很反感。那时因为我们八路军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序列中,所以团长以上都印有名片,我听说此事后,就想着自己可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两天后,毛主席的秘书来电话,说毛主席准备接见我,让我快去。当时毛主席住在延安城北门内三个石窑洞内。我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向主席住的窑洞快步走去。我到后,毛主席秘书说,你在我这里先坐一会,毛主席正在和张主席谈话。(张主席即张国焘,在这之后不久,四月份清明节时,张国焘借口到黄陵扫墓叛变)。我坐了一会,就看见张国焘从主席住的窑洞出来走了。秘书便叫我到主席住的窑洞去。
我一进门就看见主席正手拿烟卷站着沉思,我立正向毛主席敬了一个军礼,并说:“报告主席,我是警备六团王兆相”。毛主席笑着走过来,一边伸手,一边笑着说:“知道,王兆相同志你好啊,快坐下,滕代远同志说你来延安学习,这很好嘛……”我开始还有点拘谨,看到毛主席是那样平易近人,那样诚恳、热情,我紧张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了。
毛主席问了许多晋西北根据地和神府根据地的情况,从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对前线、对晋西北根据地情况了解很多,也很细。记得当时我在汇报时,有些问题没讲清,没讲透,主席很快还做了纠正。
对神府根据地的情况也是如此。记得当我谈到神府根据地的创建及红军如何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无私的献身精神,粉碎了白军的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由刚初建时7个人的特务队,逐渐发展壮大成支队、团、师和几个游击支队,成了一支使敌人丧魂失魄的有战斗经验的红军部队,根据地也扩展到神木、府谷、佳县、榆林和山西沿黄河几个区,东西宽150里,南北长400里,人口在14万以上的红色根据地时,主席深情地说:“神府苏区根据地人民为创建和保存下这块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你们能紧紧依靠群众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力量,为革命事业培养、保存了一大批党和军队的好干部,这是很大的成绩。现在这块根据地已成为晋西北八路军抗击日寇的稳固后方,也是保卫延安的北大门的重要地区。神府人民在人力、财力上对晋绥边区前线的支援很大啊”。
我细心地聆听着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心情激动万分,全身热血都像沸腾了一样。我想着那些为了神府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牺牲了的亲人和战友,那些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和出生入死的红军战士们,他们的血没白流,毛主席关怀着他们,人民会永远怀念他们。
在讲到神府红军独立师一直打到米脂时,主席笑着说:“你们在敌人重兵封锁、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师一直打到米脂,让敌人的报纸登出你们仍在战斗中,这很好嘛,中央也是从报上才知道了你们的情况,马上就和国民党各部队作了交涉,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你们的围剿…..”不过主席也说:“你们打到米脂后,当时应该继续往南打,不应停下来吗,怎么又折回神木了呢?…..”
主席还问我:“你们为什么叫神府红军根据地?你们在府谷、神木、佳县,以及山西沿黄河几个区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红军的活动区域达到榆林、米脂等地区,‘神府’这两字没能包括全部地区嘛,我看可以叫‘神府佳榆’根据地更妥一些嘛!”
当我汇报到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时,曾奉贺龙师长指示,与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军长进行了礼节性拜访,何柱国军长与我交谈中曾提出,请八路军派政工干部到他的部队去帮助整顿队伍。何军长还讲:“中央军派来的政训处干部都是些特务,起不了好作用,只会搞特务监视和破坏活动。”毛主席听到这儿,手拿烟卷,若有所思地说:“他是这样提出的吗?这说明他看出了问题,在国民党部队和东北军里,确有不少将领是要求抗日的,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打内战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里一些顽固派不断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排除异已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自食其果。今后对国民党军队要多联系,应不断地去争取国民党左翼和中间力量联合抗日。多宣传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口号。你能和何柱国军长谈到这样就很不错嘛。”
我全身贯注地聆听着主席的一字一句,主席精辟、浅显而又深刻的对统一战线的阐述,我听起来是那样振奋,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大道理啊。我又把贺老总在我临走时托我转达给毛主席的话也讲了。我说:“主席,贺老总让我转告您,我贺龙不识几个大字,也请求去学习提高提高文化知识,到苏联去学习或驻抗日军政大学都可以……”毛主席听后慈祥地笑了。主席一边抽烟,一边笑着说:“啊!他不能去学习,晋西北根据地的任务很重嘛,工作不允许他贺老总去学习啊!”
在我汇报中,主席总是笑着点头,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我们谈了约一个多小时。毛主席对我说:“你文化低,这次进学校要好好学习,你在根据地的创建中做了不少工作,有许多好的经验,但不会总结,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学习的机会,学好了才能更好地去做工作嘛……”。
这时秘书进来说,有人要见主席。我站起来说:“主席,我一定好好学习!”毛主席笑着握着我的手说:“好!”我向毛主席敬了个礼,转身向门口走去。毛主席一直把我送到窑洞口才回去。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没想到毛主席是那样平易近人,是那样诚恳热情,对我又是那样的关心。我文化水平低,不会作什么笔记,许多事都是靠脑子记,所以在整个汇报、谈话中,对一些数字和个别问题没讲清,没讲对,主席就很快帮我作了纠正。我深深感到主席洞察、了解、分析事物是那样透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党政军素质,不辜负毛主席对我语重心长的教导。

二、抗大的军事学习生活
(一)在抗大第三期高级班的学习生活
总部通知我到抗大报到,那是在1938年3月份,毛主席与我谈话后不几天的时间,肖劲光司令员送了我一套衬衣和外衣,给了我十块钱,我就去抗大报到了。
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罗瑞卿。我去时,许光达教育长接见了我,他告诉我抗大校内目前有一个第三期高级班,现在已学一段时间了,但还没结业,你先到这个班学一段时间,等第四期高级班成立时,你再转到第四期从头学起好了。我说:“行,只要让学习就行。”
第三期高级班班主任是李寿轩,学员大部分是四方面军长征过来的高级干部,记得我们一个小组的同志有杜义德、王宏坤、王树声等,我和杜义德睡在一个土炕上。其他许多我都记不起来了。在这个班,我只学了两个多月就结束了。
在这个班里,我听过陈伯钧讲的战略战术和其他领导同志的许多课程。影响最深的是毛主席讲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报告,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这个还不会记笔记、文化水平很低的人,都记忆犹新。
我记得主席讲道:“……你们许多同志不了解我们现在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认为现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有的同志认为就是共产主义革命了,这是不对的。”他举了个例子说:“在红军长征时,我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找一些报纸、书籍来看。一天我到一户地主家,看有没有报纸或书籍之类东西,地主的老太太一见我就说,昨天他家已被共产了,这些东西都没了。你们看,她就把我们说成共产主义了。我们许多干部也说不清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大家应该明白,我们现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更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还得许多年……目前,我们对爱国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是不会进行打击的,我们打击的是封建地主买办、官僚、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如果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得走许多路,就像我们从这里出发要转个湾才能走到延安北门口外一样,不是一步或几步就能走到的…..”
听过毛主席这次讲话后,我才明白,我们过去打土豪、分田地,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次讲话对我影响很深,所以至今过去几十年了,主席讲话的大概意思我还能想起一些。
主席的报告很大众化,很容易听明白,他就像和你拉家常话一样,慢慢讲解,对我们这些没啥文化水平的工农干部来说,听起来格外亲切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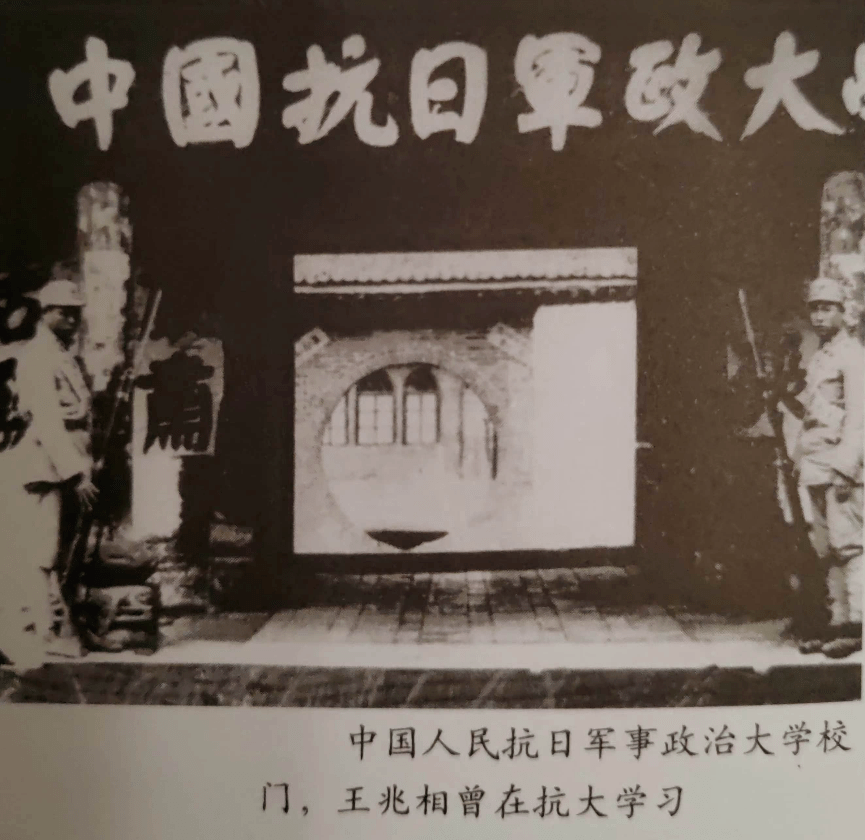
(二)瓦窑堡大队的学习生活
1938年4月份,抗大第三期高级班正式毕业了,许光达教育长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抗大四期不成立高级班了,只在“抗大”瓦窑堡大队成立一个红军干部支队,你到那里去学习怎么样?我说“当然可以”。这样,我又转到瓦窑堡大队学习。
当时,瓦窑堡大队队长是苏振华,政委是胡耀邦,一支队队长是詹才方,副队长徐德操兼二队队长,一支队是军事干部队,二支队是政治干部队。我被分在一支队一区队一班,先后担任过班长和区队长。我们上课的地方原来是国民党骑兵的一个大的马厩,经稍加整理就成了我们的课堂。几十个人挤在这个马厩里,三块砖头垫起来当凳子,膝盖就是可移动的桌子。
在这里既学习文化政治课,又学习军事课,班里学员大多是各地区来的红军时期的军事干部,文化水平都不高。我这个只读过三年半书的人,还算个小知识分子呢。所以班上还让我给大家讲文化课中的一些成语和小故事。
我在参加革命前,种地放羊多年,那时一边放羊,一边拿点武侠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等看,字不认识就问人。实在找不到人问时,我连猜带蒙也了解了一个大概。那些年,我稀里糊涂也看过不少书。没想到在这个班里,我这点文化水平倒有用了。这个班还有一些同志一天学也没上过,我比他们就又强多了。
我当区队长,负责带队出操,做军事动作。那时军事班主要是学军事课,教材就是苏联红军的战斗、战术条例,排、连、营、团的战术。记得我们还到野外进行了一次实战演练。1938年8月1日前,全大队还开展了一次迎“八一”学习军事技术运动,全队苦练站、跪、卧倒的射击战斗动作。班上虽然都是各级连、营、团以上干部,但大家学习上都很刻苦。记得那时衣服少,我们连换穿的衣服都难找到,做战术动作时,我的裤子磨破了,就干脆把膝盖以下剪掉,当做短裤穿。结果在练习战术动作时,膝盖都磨出了血,结了厚厚的茧子。我们政治课主要学习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在抗大四期的这段军事政治学习生活,是我自参加红军以来第一次比较正规的学习。在这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学到11月底12月初时,形势有了变化。据情报说,日本鬼子即将进攻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央决定我们和敌人换防,敌人如到陕北,我们就到敌人后方去,到他们的心脏地方去。所以决定抗日军政大学搬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时我们正在学习团的战术条例,一天,罗瑞卿副校长和训练部长陈伯钧来瓦窑堡大队讲了目前的抗日形势、日寇的动向及中央的战略部署,同时讲了学校准备如何搬迁,有的班将提前结业等等。罗瑞卿副校长讲话很诙谐,逗得大家笑个不停。陈伯钧讲到军事队时说,军事队课程还没学完,但形势要求也只有提前结束回部队了,你们其中有一些干部已有许多实战经验,像你们队中的贺炳炎、王兆相,这些同志已经参加过多次战斗,回部队仍可以在实战中学习提高嘛。就这样,我们于12月结束了在瓦窑堡的抗大生活。
这段抗大正规化的学习生活对我帮助很大,给后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东北解放战场及南下各个解放战场上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抗大生活,使我多年来的游击战生活养成的非正规化习惯得到一定的纠正,培养了过军事集体生活的好习惯。更主要的是,通过第三期、第四期抗大紧张的学习生活,我在军事知识上有了较大提高,同时也懂得了不少革命理论知识。
(三)在马列学院的学习生活
1.在警备六团回延安。
1938年12月,在抗大瓦窑堡大队毕业后,我急着想上抗日前线,回晋西北自已的老部队警备六团去。
总政组织部方强同志通知我先到延安留守兵团去见萧劲光司令员。在延安,萧司令告诉我,警备六团最近决定调到延安来,你现在回去路上拖得时间长,还没到晋西北根据地,警备六团就该出发了,你不如就在延安等一段时间吧。我说:“那我这段时间干嘛呢?”萧司令说:“我看你不如先到党校或马列学院再学习一段时间,毛主席不是也让你多学习嘛?正好这也是个机会。”我说:“我可真想马上回部队上抗日前线去。”萧司令说:“那好,你去见见谭政副主任,看他的意思如何?”然后,他给我写了封信,让我带给谭政副主任。正好信也没封口,我也实在好奇,在路上就拿出来看了。信的内容大致还是留我在延安学习,暂不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延安等警备六团回来。谭政副主任看罢信,笑着说:“你都看了吧,萧司令的意见我同意,我看你还是留在延安等部队吧。我们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滚过来,滚过去,不容易找到学习时间,我还专门到莫斯科学习过一回,你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学习,我看这样很好,我先介绍你到马列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吧。”就这样,我出了抗大校门没几天,又于1938年12月初进了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2.中央领导当教员。
马列学院是中央最高学府,院长是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同志,副院长是王学文,一个老学究似的经济学家,人非常和善。这所学校工作人员还不到20人,教员均由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兼任。学员是来自各地参加革命的高中、大学及留学回来的知识青年和参加革命较早的团以上干部。我这个从小放羊、只念过三年半书的军事干部到这个最高学府来学习,当时心里真有点胆怯。但那时毕竟年轻,什么也不怕,况且认为只是暂时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等警备六团回延安后就走。但没想到警备六团因故一直没回到延安来,而我在这里一学就学了一年半时间。
到马列学院后,又赶上第二期没毕业,第三期还未招生,学院又决定我先在第二期这个班学习,第三期开课后再转到第三期去。当时马列学院每期只有一个班。于是我又只好插班到第二期听课。
二期、三期这两个班的学员中,有参加革命较早的阎红彦、谭余保、徐海东、张秀山、汪东兴、马宏等同志,也有许多文化水平较高的年青知识分子。当时,丁玲、江青、孙维世、扬拯民等也在这个班学习。1939年4月份,第三期开办后,我又转到三期学习了。
当时,我们的教室是由一些柱子搭起的草棚顶大房子,每期100多人都是在此上课,没有课桌,和抗大学习时一样,膝盖就是每个人的课桌。两边放几块砖头,上面搭块木板,就是我们的凳子。
学校的课程很多,刚开始我听起来非常费劲,就像整天驾在云雾里一样。记得教员和同学们讲什么偶然和必然、相对与绝对,我都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张闻天同志和艾思奇同志都鼓励我说:“王兆相你文化低,也别急,听不懂可以多问,这不是短时间能补上来的,今后要多看点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之类的书籍,这样可以增长许多文化知识。”在学习上我是很用功的,我完全靠眼看、耳听、脑记,动手记笔记的能力很差。即使这样,我当时还是觉得有关马列主义、党建、新民主主义、世界革命史等知识,我学得还是不错的。政治经济学、哲学比较难懂,学起来也相当困难。
政治经济学由王学文副院长讲,他像一个老学者,和孔祥熙、马寅初都是同学,常给我们讲他们之间的关系。他讲课很有耐心,每次都怀抱一堆书放在讲台上,慢慢地讲。艾思奇同志负责哲学课。他们都很关心我,但我听他们课时,总被绕来绕去搞糊涂。我和同学们一样,最喜欢听毛主席讲的新民主主义和陈云讲的党建课。陈昌浩讲的世界革命史也很吸引人,他语言丰富,故事性也强,大家很爱听。毛主席和陈云讲的都是我们革命斗争中的现实问题,通俗易懂,语言生动。还有张闻天讲的是战略策略,王明讲统一战线,陈伯达讲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杨松讲中国革命,吴黎平讲马列主义。许多课程我开始学习时总摸不着边,很吃力,后来在首长和同学们帮助下,逐渐走上了轨道,基本能跟上学习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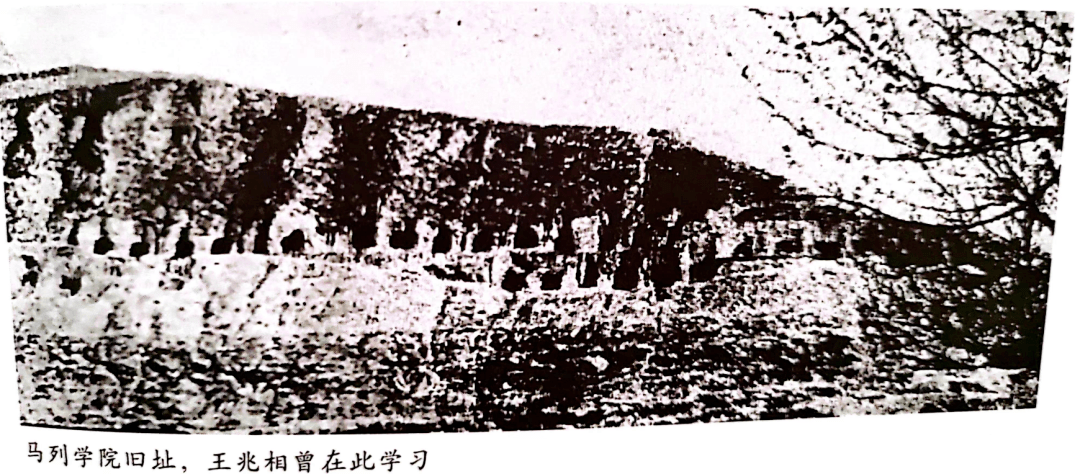
3.听陈云讲党的建设课。
陈云同志讲的党的建设对我影响很深,他讲建党历史、党的工作方法、党的任务、党内思想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等课程。
记得有一次他讲党内思想斗争时,批判了一些不正确方法。他说,在我们党内思想斗争中,有些同志首先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动不动就给对方扣大帽子,特别是有一些年轻的同志,他们像我这样,这时陈云学着把自己的拳头举过头顶说,他们在批判别人时,把拳头举得高高的,把帽子扣得大大的,不让被批判者说话,这样能让别人服气吗?陈云讲,批判应对事不对人,不要动不动就不让人说话,拿拳头把别人吓住,拿大帽子把别人压住。应该首先把对方的缺点甚至于错误都摆到桌面上来,用事实来说明问题,由被批判者本人按照他的缺点、错误的大小,找一个最适合他本人的帽子去戴,你给他强加的帽子不是大就是小,他戴着也不舒服吗。
当他讲到要纠正党内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时,针对马列学院内一些议论,谈了绝对平均主义是错误的。他说,马列学院招生是有一个原则规定,但在目前情况下,有些特殊问题我们只能特殊处理。我们这些年来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不少革命同志,他们留下的子女我们不照顾谁去照顾,让他们到马列学院来学习有什么不对的?这也是为革命培养人才嘛(系指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等人)。至于有人对一些文化低的老同志来马列学院学习有看法,认为只有大知识分子才能到这儿来学习,你们知道这些老同志都是在战争中冲杀出来的,你们可以去数数他们身上有多少伤疤,他们文化低,更应该学习提高一下文化水准,这样不就可以为革命做更多的事嘛。
在讲培养干部的问题时,陈云同志说:“我们其中个别年轻的同志认为自己是读过高中,上过大学,留过洋的,现在又在中央最高学府学习,将来毕业出去,理所应当给个省级干部职务当。我说,那是不行的,马上让你去做个省级干部,你是干不好的,对你们也不好。你们有文化,有理论,但欠缺实际革命斗争经验。工作上的经验靠积累,万丈高楼平地起,你们出去后应先去当区干部、支部干部,以此来积累经验和工作方法,将来才能做更多大事。”
在讲党的工作方法时,陈云同志举了一个例子,着实让我们笑了一遍。他说:“我们有一个部队,为了做抗日友军的统战工作,曾派一个旅长到相邻的国民党一个与我们还关系可以的旅长那里去做友好拜访。组织上是让他去联络感情,做统战工作,结果我们这位同志去后,坐下就给别人讲抗日的大道理,根本不容别人有说话的机会。自己讲了大半天,最后问别人有什么说的。别人莫名其妙,像听训话一样昕了半天,正丈二和尚模不着头脑呢,也不知我们这位旅长来干什么?还能有什么可说的,结果我们这位旅长抬起屁股就走了。这哪是去联络感情?哪是友好谈话?谈话,是双方说话,你谈,别人也能谈,而且应耐心地诚恳地听别人说,绝不能武断似的只你一个人说。你们出校门去工作后千万要注意,在谈话中一定要多听取别人说什么,让别人把话说完,可别像那个旅长一样,自已说完抬起屁股就走人。”
在讲党内斗争时,他讲为什么我们本来还好的一些同志,后来也走向犯错误甚而犯罪的道路呢,这绝不是他生来就坏,而是慢慢养成的,譬如我们有一个司务长,他负责会议招待,当人都走光后,他看到桌子上有香烟,就顺手拿了一支抽了,也没人说什么。第二次招待后,他又拿了两支烟抽了,这回也没人说什么。后来,他干脆把剩下的一盒烟也放到兜兜里了。就这样,她的行为始终没人理,没人批评,结果他胆子越来越大,什么都敢拿,最后成了贪污犯。如果一开始发现我们就提醒他,批评他,他也就不会后来成为贪污犯了。
一年多时间,我听过陈云同志很多课,印象很深,他不但课讲得好,而且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我也是难以忘怀的。
记得有一次下课后,正赶上外面下着大雨,陈云同志夹着书走到门口,停下来卷起裤腿,把鞋脱下来夹在胳肢窝里,打起伞往外走。正好我也走到门口,惊奇地问:“陈部长,你怎么脱鞋光着脚在水里走?”他笑了笑说:“这样好,鞋沾上泥水容易坏,又不好洗,脚脏了,回到家一冲一擦,不就干净了嘛!”他就像没事一样在雨水中大步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很感动。我们的中央首长,不但在政治思想文化理论上是我们的老师,他们在实际生活、工作行动上,也是我们的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
4.收获。
在马列学院一年半时间的学习生活,有许多课程,我由听不懂到逐渐听懂并理解,这花费了中央首长们不少心血。通过学习,我深深感到自己眼光看得远了,视野更开阔了,对共产主义,对党的信念更坚定了,对抗战胜利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多年来,我一直是在陕甘、陕北、晋西北战场上与敌人浴血战斗,所以思想深处一直有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战斗中的胜负都离不开枪杆子。到延安后,毛主席及其他各位首长都反复教导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提高政治文化理论知识。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是如何关心爱护我们这些工农干部,同时体会到了学习政治文化理论知识的实际意义。
(四)在延安印象最深的两次大会
在延安学习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除了在延安抗大、瓦窑堡抗大大队和马列学院学习外,还参加过中央和边区党、政、军部门组织的多次会议,直接聆听了许多中央首长的讲话,受到很大教育。印象最深的是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和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1.边区参议会。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宣告正式成立,并于延安举行第一届会议。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在会上讲话,并发出“边区人民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报告,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一些提案及法规,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为副议长。同时,选出了林伯渠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我也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
这次边区参议会正好是我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召开的。我是马列学院选出的代表,所以分在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与毛主席、张闻天、柯庆施、陈伯达等中央领导同属一个组,共有十多个同志。当时中央领导工作很忙,不可能天天到会,而我和为数很少的几个同志就成了会议上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常驻代表。大会秘书长曹力如同志通知我是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组长。我当时觉得不妥,自己干不了,就向曹力如同志提出:“代表团组内都是中央首长,我既不会说,又不会写,我可当不了这个组长。”曹力如秘书长耐心地向我解释:“你放心,让你当这个组的组长,是我征求了大家意见后决定的,再者这些中央首长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们去处理,不可能每天都来参加会,有事通知他们一下好了。”我说:“我连个信都写不好,怎么通知他们?”曹力如笑着说:“这你放心,我找人帮你去干好了。”整个大会期间倒没啥事,忽然有一天大会秘书处通知说,一些地方的同志给大会送来一些水果和土特产,决定分给每个代表。正好那天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大多都没来,我只好托人给毛主席及每位中央领导写了封信,签上我的名,曹力如派人一一送了去。
有一天开大会,我们中央党团代表小组按划分好的地方就坐。我看到毛主席来了,正好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我立即站起来说:“主席,你好!”并向他敬了个礼。主席看到我说:“王兆相同志,你好,你派人送来的通知和礼品,我都收到了,谢谢你啦!”坐下后主席又对我说:“王兆相同志,你是我们的组长,我有事不能经常来参加会议,我向你请假。”我马上笑着说:“你是首长,有事还向我请什么假。”主席马上接着说:“啊!哪能不请假,不请假是不对的,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吗。”我听着主席的话,感到自己该学的东西太多了。毛主席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从不把自己放到特殊的地位上。在交谈中,主席问我:“会议开得好吧?”我简单地向他讲了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告诉他,听了你和其他首长在会上的报告,很振奋人心,收获很大。这时,主席又关心地问我在马列学院的学习情况。他又一次讲:“你过去在战斗中、游击战中有很多好的经验,但你文化低,不善于总结提高,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提高文化理论知识,特别是党的理论政策方面的知识。学习上不但要学好,而且要会写出来让别人去看,只有会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更快提高自己,那工作也就好做了……”后来,我回想起毛主席的话,这实际上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阐述的内容,把实际上升为理论,理论再应用到实际中去检验的道理。
2.边区第二次党代会。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县徐家沟(真武洞)举行。我作为中央机关选出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大会。在这次会上,我被选为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我和肖三、陈伯达同住在一个窑洞的土坑上。
会上,高岗作了《关于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报告。陈云、李维汉等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毛主席也作了政治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谈了抗战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建设,向边区党的各级组织提出“提高自己,帮助别人”的任务,号召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
主席谈到统一战线工作时,批评了一些错误观点,强调统一战线也是有斗争的。他说:现在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又掀起了一股反共高潮,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回击,特别是对那些国民党的老顽固派,一定要在揭穿他们阴谋的同时,狠狠地打击他们。我们的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又说:我们在反对顽固派时,也要做到有礼、有利、有节。斗争要有策略。在斗争中搞好统一战线工作。
主席在谈到目前党的工作时,坚定地说:“我们党近来抓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抓边区部队建设,在边区扩大留守兵团建制,充实留守兵团。”说到这里时,主席把拳头举过头顶,使劲挥着拳头说:“留守兵团就是我们的铁拳,如果没有留守兵团这个铁拳,没有萧劲光同志在这里,我们能在这里坐下来开会,能坐得安稳吗?所以我们要感谢萧劲光同志,感谢留守兵团的指战员们。”此时,萧劲光司令员就坐在台下,我感觉到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向萧司令。毛主席又大声讲:“现在的情况就是谁的拳头硬,谁的话就有人听,否则谁也不会听你的话。”
主席说:“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党最近以来大量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宝贝,是我党我军的一批新生力量。”这时,我又看到毛主席挥着拳头说:“同志们,我党我军发展后继有人啦,这也是我们党内对文化和知识有了进一步认识的重大体现……”
主席的讲话很是震撼人心,参加会议的代表个个都很激动。我坐在台下听着主席铿锵有力的讲话,感觉到浑身的热血都沸腾了。
(五)到抗日最前线去
1940年5月,我从马列学院毕业,即将走上新的岗位。在延安经过8个月的抗大学习,一年半左右的马列学院学习,我不但在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上有了提高,而更主要的是政治思想、工作方法、认识问、分析问题等许多方面所受到的教益,是难以用笔描绘出来的。通过二年半左右的学习生活,我的思路和胸怀开阔了。我认识到自己应该到更广阔、更艰苦、最需要我的抗日最前线去,不能总是守着自己多年的老部队和战斗了多年的家乡。所以在毕业前夕,我就主动向总政治部谭政副主任提出,希望到最艰苦的抗日前线去。后来,谭政副主任找我谈话,他说:“你的这种要求和决心是很好的,警备六团在晋西北,原准备让你去接阎红彦的警备三团工作,既然你提出到其他根据地去,我们研究了一下,可以让你到新四军去工作。”我说:“行,只要让我离开陕北后上前线,到哪都行。”因我当时己被马列学院选为参加“七大”的代表,我又问:“七大”何时召开。他告诉我,你可以参加完“七大”后再走。
我又到留守处萧司令员那里,向他报告“总政同意我到新四军去工作”。萧司令员听后感到有点突然,他问我:“怎么叫你去新四军?谁告诉你的?主席知道吗?和你都谈了些什么?”我告诉他:“离开延安到其他根据地去,是我自己向总政提出的,主席是否知道我不了解。”萧司令听后“啊”了一声,接着说:“我们原想你对陕北情况比较熟悉,在这里工作起来方便些。警备六团不回延安了,准备让你去接警备三团的工作,现在你要求到其他根据地去,当然陕北的同志也不一定非留在陕北工作,换个工作战斗的环境,离开自己熟悉的部队、熟悉的地区,也是个更大的锻炼。”
5月份,我在马列学院正式毕业。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同志通知我先到延安小砭沟招待所住下,等参加完第七次党代会后再去新四军。我在小砭沟休息了1个月之久,其中除有时仍参加一些边区党、政、军的会议外,就是参观学习。后来总政通知我,去新四军的路不通了,让我先到留守兵团的一些部队去参观,当然这也是一种学习。
一天晚上,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他说:“新四军目前去不了,道路被封锁无法通过。你是“七大”代表,但中央决定“七大”延期召开,何时召开还没定,中央意见,要你去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你看还有什么意见?”我马上回答:“我完全服从组织决定,到山东抗日前线去。”胡耀邦同志说:“那好,既然你同意,明天你就走如何,因为送给晋东南的一些物资已经准备好上路了,你和他们一块走,部队送你们也方便。”我问他:“我爱人在延安‘女大’学习,能否与我一块走?”胡耀邦同志说:“你可以带爱人一块走,中央刚作出决定,团以上干部可以带家属到敌后去工作。”我说:“那好,请胡部长把我爱人从‘女大’调出来,我们后天出发成吗?”胡耀邦同志说:“行,我明天就把你爱人调出来。”接着,胡部长又说:“不过有件事,真对不起,本应该配给你枪支、弹药、马匹,但总政本身也很困难,好在你就是陕北人,自己去活动枪支、弹药、马匹、人员,我负责批给你们路费。”我说:”行,请部长把一切手续和路费帮我办好就行了。”
第二天上午,我就找到王世泰同志,他给了我一匹马,一个马夫。我原来就一直带着一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枪支弹药我从留守兵团全搞到了,这样我们就成了四个人,两匹马。当天下午,胡耀邦同志就批给了路费,办好了一切手续。
第三天清早,我们在战友们的欢送簇拥下,从小砭沟一直走到桥儿沟,大家才依依不舍地道别。我骑在马上,回头望着仍站在那里的战友,望着远处那高高的宝塔山,望着那抚育了无数英雄儿女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我回忆起与战友们创建根据地时的艰苦战斗历程,回忆起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的日日夜夜,回忆起毛主席及各位中央首长对我的关心和谆谆教导,我默默地向崇山峻岭发誓:“毛主席,各位首长,战友们,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教导,好好学习,英勇战斗,为了祖国,为了党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乃至生命。”
(王兆相之子王延生整理)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兆相(中共七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任工程兵学院院长等职)
整理:王延生(王兆相之子,1940年出生于延安,高级工程师。1961年7月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后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714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714所工会主席。退休后曾任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理事,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名誉顾问)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