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人】家国情怀与学术时风的缠绕 ——评张栻《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 潘忠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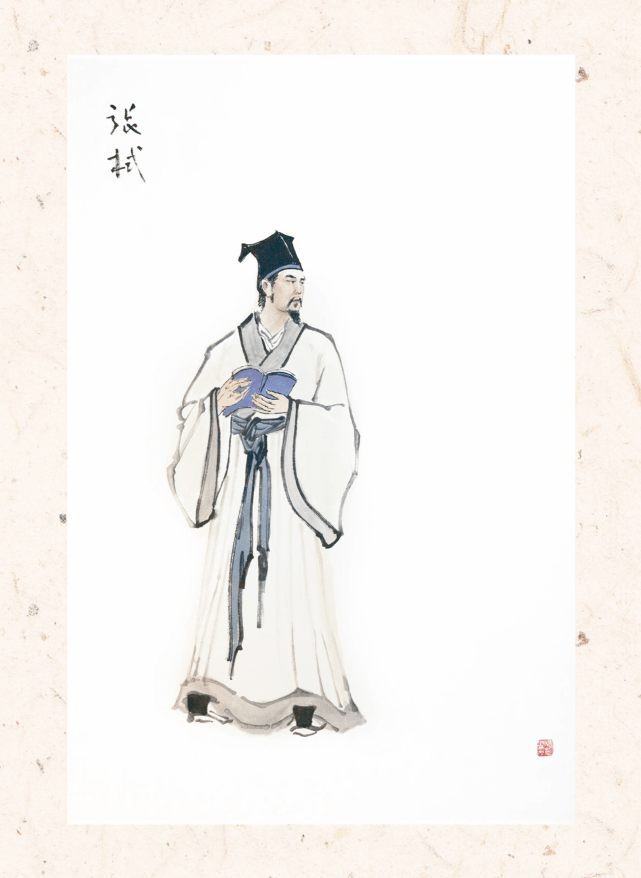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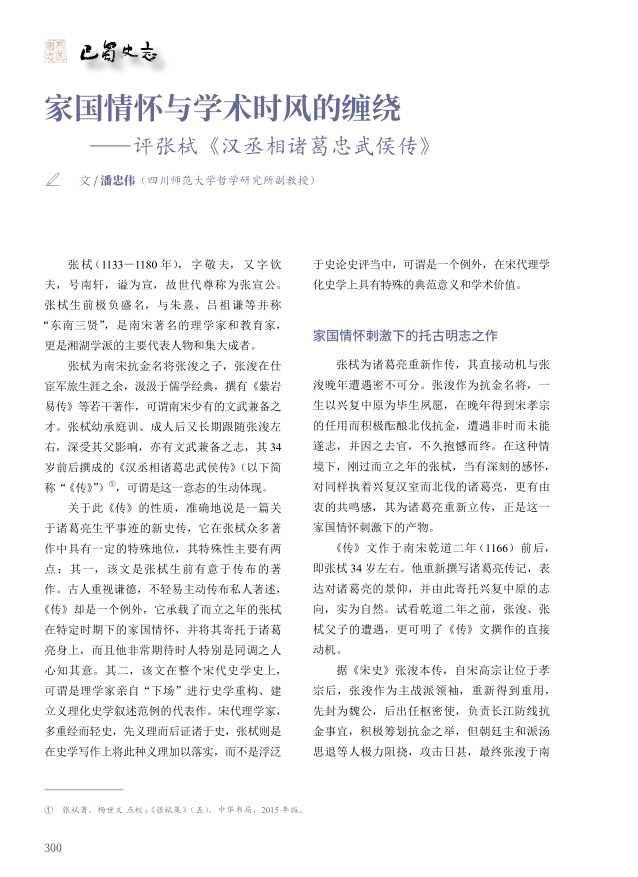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家国情怀与学术时风的缠绕
——评张栻《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
潘忠伟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字钦夫,号南轩,谥为宣,故世代尊称为张宣公。张栻生前极负盛名,与朱熹、吕祖谦等并称“东南三贤”,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更是湘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

张栻为南宋抗金名将张浚之子,张浚在仕宦军旅生涯之余,汲汲于儒学经典,撰有《紫岩易传》等若干著作,可谓南宋少有的文武兼备之才。张栻幼承庭训、成人后又长期跟随张浚左右,深受其父影响,亦有文武兼备之志,其34岁前后撰成的《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以下简称“《传》”),可谓是这一意态的生动体现。
关于此《传》的性质,准确地说是一篇关于诸葛亮生平事迹的新史传,它在张栻众多著作中具有一定的特殊地位,其特殊性主要有两点:其一,该文是张栻生前有意于传布的著作。古人重视谦德,不轻易主动传布私人著述,《传》却是一个例外,它承载了而立之年的张栻在特定时期下的家国情怀,并将其寄托于诸葛亮身上,而且他非常期待时人特别是同调之人心知其意。其二,该文在整个宋代史学史上,可谓是理学家亲自“下场”进行史学重构、建立义理化史学叙述范例的代表作。宋代理学家,多重经而轻史,先义理而后证诸于史,张栻则是在史学写作上将此种义理加以落实,而不是浮泛于史论史评当中,可谓是一个例外,在宋代理学化史学上具有特殊的典范意义和学术价值。
家国情怀刺激下的托古明志之作
张栻为诸葛亮重新作传,其直接动机与张浚晚年遭遇密不可分。张浚作为抗金名将,一生以兴复中原为毕生夙愿,在晚年得到宋孝宗的任用而积极酝酿北伐抗金,遭遇非时而未能遂志,并因之去官,不久抱憾而终。在这种情境下,刚过而立之年的张栻,当有深刻的感怀,对同样执着兴复汉室而北伐的诸葛亮,更有由衷的共鸣感,其为诸葛亮重新立传,正是这一家国情怀刺激下的产物。

陕西宝鸡五丈原诸葛亮庙
《传》文作于南宋乾道二年(1166)前后,即张栻34岁左右。他重新撰写诸葛亮传记,表达对诸葛亮的景仰,并由此寄托兴复中原的志向,实为自然。试看乾道二年之前,张浚、张栻父子的遭遇,更可明了《传》文撰作的直接动机。
据《宋史》张浚本传,自宋高宗让位于孝宗后,张浚作为主战派领袖,重新得到重用,先封为魏公,后出任枢密使,负责长江防线抗金事宜,积极筹划抗金之举,但朝廷主和派汤思退等人极力阻挠,攻击日甚,最终张浚于南宋隆兴二年(1164)去职,改任醴泉观使这样的闲职。张浚行至江西余干时,得病不起,临终手书遗言给张栻、张杓二子,说:“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由于这个缘故,绵竹张氏就有了湖南一脉。
张浚抱憾而终,未能兴复中原,对于孝子忠臣的张栻而言,刺激当是极深。张栻营葬父亲之后,就立即报疏给孝宗,其中提到:“吾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异时朝廷虽尝兴缟素之师,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忱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今虽重为群邪所误,以蹙国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开圣心哉。谓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敌不难却矣。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济哉?”这里面既有对孝宗主和的委婉劝谏,更有对不能不报不共戴天之仇的愤恨之情,最重要的是有“坚志”“纯心”横贯于行文当中。
此种心态在《传》文之末的张栻自述中得到充分印证。他说自己为诸葛亮立传的原因,其直接感召来自于诸葛亮“汉贼不两立。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的“本心”。对于诸葛亮此种本心的形成,张栻还以文学想象的笔调加以形象描绘,说诸葛亮“自幼读书,读观大略,晨夜从容,抱膝长啸,其胸中所见,岂浅识所能窥哉!”这是张栻以自身经历来塑造诸葛亮的少年求学行迹。当然,《传》文的撰成及其学术史意义,不仅仅表达了张栻的家国情怀,也不仅仅是张栻对其父张浚抱憾而终的某种不平之鸣,而是它的出现和产生,也是理学家自觉建构义理化史学体现的实践之作,这点张栻也有充分意识;而《传》文的读者,也是从义理角度衡量诸葛亮的得失成败。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该篇也是南宋理学家构建义理化史学的范例,也应从这一角度对《传》文的得失加以评述。
理学家义理化史学观的历史写作典范
张栻所撰的《传》,与《三国志》诸葛亮本传的最大不同点,除吸取、采纳并系统整理包括裴注及其他文献在内的大量史料以丰富其行迹事功之外,更在于具有鲜明的义理立场,可谓是宋代理学家义理化史学的实践典范。这种义理化史学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用春秋笔法以寓褒贬之论;二是以义理为取舍史料、评价人物之准绳;三是凸显天理与人心的交汇点以神化诸葛亮。

所谓义理化史学的基本内涵,似可用朱熹一句话来概括:“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此语极为高明,所谓“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就在于天理之正与否,所以他又说“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即义理化史学的核心要目是透过史实而辨证是非于毫厘之间,进而完全升华天理的“是”与摒弃人欲功利这些“不是”。这一义理化史学观的前提,是要存得天理,张栻在《传》文所附的自序中不断赞美诸葛亮“配天之本心”“正大之体”“常理之大公”,充分表达以天理为正、“正义明道为贵”的义理化史学的根本立场至于如何辨析义理的“是与不是”,张栻在《传》文书写上主要是通过三方面加以落实和体现。
一是以春秋笔法以寓褒贬之论。宋代史学家习惯改变旧史本文而易以新语新词,此种风格骤然视之似乎无足轻重,但所系关键甚大。典型如欧阳修、宋祁所修的《新唐书》,与五代所修的《旧唐书》之别,即在于此。张栻所修《传》文,称呼称王之前的刘备一概用东汉朝廷官衔“左将军”,而《三国志》则常冠之以“先主”。理学家并不视此等称谓为小事,这是辨析毫厘而求得是非的“大伦理”。
二是以义理为取舍史料甚至评价人物之准绳。张栻极力塑造诸葛亮的正大形象,认为他代表某种“常理之大公”,不过,《三国志》本传明言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对头脑中充满理学门户之见的张栻来说,却是一大难题。对此,他直接将这些说法概括为诸葛亮“不足学”的地方,并将这些与诸葛亮学术风貌息息相关的史料记载统统加以删除。朱熹对此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该如实照录,张栻在自叙中则以《出师表》忠心事主的意态为据,认为诸葛亮喜好申、韩之术的历史记载不可尽信,并发挥出如果让诸葛亮“得游于洙泗之门,讲学以终之,则所至又非予所知”云云,这不仅仅是史论,而是历史想象了。
同样,对一些裴松之已经明确表示可疑的历史文献,张栻出于义理之见,认为这些记载有利于塑造诸葛亮正大之体形象而大加援用,引为确论。例如裴松之曾对《蜀记》所引的诸葛亮与法正辩论治蜀宽严之道一事提出疑问,认为法正死于刘备之前,在刘备生前诸葛亮“未领益州庆赏刑政”,自然就不可能以“谦顺之体”代替刘备发表治蜀方略。张栻在《传》中,则以“亮佐益州,政尚严”一语为引导,详引法正与诸葛亮辩论之语。言外之意,此事为确,张栻似乎就不在意从义理之“是”中辨证史实之或许“不是”了。
三是凸显和强调诸葛亮为天理和人心的交汇点,是忠臣的典范。诸葛亮在历史中的定位形象,主要有3个特点:智、治和忠。所谓智,是说他致远深思,以谋略为长;所谓治,是说他理政有方,恩威得当;所谓忠,是说他竭尽臣节,死而后已。历史上对诸葛亮的上述3个面相,有所侧重。例如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叙述,虽然3个方面都有涉及,但当时重视的是“才”这一名目,所以在这一名目下他有一句著名的评价:“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于将略。”
这一评语一直备受瞩目而引发不少争论。张栻以义理化史学为根本立场,对诸葛亮的评价则是以“忠”为核心、以“治”为主干、以“智”为铺陈,其行文叙述,无不彰显诸葛亮之“忠”和“本心”,至于他的谋略之智与施政之才,都要本于“忠”。
总而言之,如果将《传》看作是理学家义理化史学的写作典范,那么它的确是集中体现了这种史学写作的优劣得失:其优点在于主旨鲜明,能够抓住“亮之异美,诚所愿闻”(裴松之语)的普遍心理,将诸葛亮的正大光明形象不断加以凸显和提升;其缺点在于不拘小节,对史事史料的真伪辨证,并不多加留意。由此之故,那么今人对张栻所撰的诸葛亮《传》,既要看到他在撰写时特定背景下的家国情怀,又要更多地关注他所阐发的“大伦理”、大是非和大情感,至于诸葛亮治蜀行迹的诸多细节问题,就留待史学家们去细心考索和辨证,而不能过多苛求古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潘忠伟(四川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