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果 ‖ 成都美女白如霜——追寻元朝诗人汪元量在成都的行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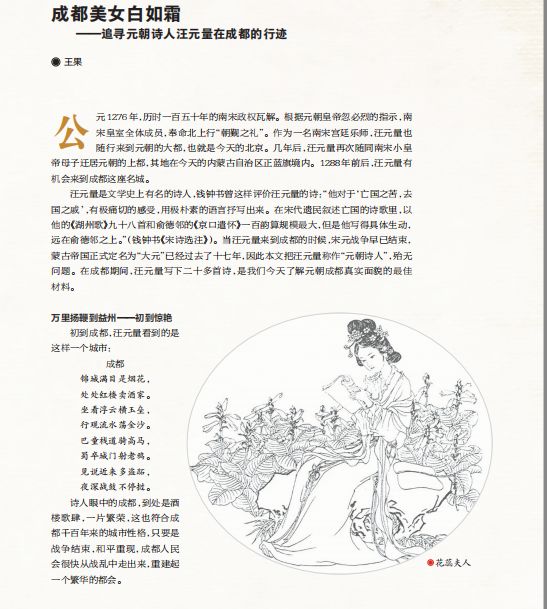
本文刊于《巴蜀史志》2019年第1期
公元1276年,历时一百五十年的南宋政权瓦解。根据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指示,南宋皇室全体成员,奉命北上行“朝觐之礼”。作为一名南宋宫廷乐师,汪元量也随行来到元朝的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几年后,汪元量再次随同南宋小皇帝母子迁居元朝的上都,其地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1288年前后,汪元量有机会来到成都这座名城。

汪元量是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人,钱钟书曾这样评价汪元量的诗:“他对于‘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有极痛切的感受,用极朴素的语言抒写出来。在宋代遗民叙述亡国的诗歌里,以他的《湖州歌》九十八首和俞德邻的《京口遣怀》一百韵算规模最大,但是他写得具体生动,远在俞德邻之上。”(钱钟书《宋诗选注》)。当汪元量来到成都的时候,宋元战争早已结束,蒙古帝国正式定名为“大元”已经过去了十七年,因此本文把汪元量称作“元朝诗人”,殆无问题。在成都期间,汪元量写下二十多首诗,是我们今天了解元朝成都真实面貌的最佳材料。
初到成都,汪元量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城市:
成 都
锦城满目是烟花,
处处红楼卖酒家。
坐看浮云横玉垒,
行观流水荡金沙。
巴童栈道骑高马,
蜀卒城门射老鸦。
见说近来多盗跖,
夜深战鼓不停挝。
诗人眼中的成都,到处是酒楼歌肆,一片繁荣,这也符合成都千百年来的城市性格,只要是战争结束,和平重现,成都人民会很快从战乱中走出来,重建起一个繁华的都会。
百花潭
万里扬鞭到益州,旌旗小队锦江头。
红船载酒环歌女,摇荡百花潭水秋。
百花潭是成都的著名古迹,杜甫就有“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的名句。可惜的是,时至今日,著名的百花潭早已消失无踪。透过汪元量的诗句,我们可以确知,至晚在元朝,百花潭这一泓水面还安然无恙,还是成都市民泛舟游览的好去处。

成都百花潭公园一角
在成都,汪元量受到很好的接待,一小队人马张着旗帜,带着歌儿舞女,载着美酒佳肴,泛舟在百花潭的秋水之间。从接待规格来看,并非是一般私人游历所能有的,似乎有官方接待的背景。汪元量是小人物,他在成都受到如此规格的接待,看似有些蹊跷,实则事出有因,本文将在稍后部分探讨这一问题。
关于当时成都的市井情况,汪元量有两首短诗涉及,其一是《药市》:
蜀乡人是大医王,一道长街尽药香。
天下苍生正狼狈,愿分良剂救膏肓。
汪元量盛赞“蜀乡人是大医王”,无疑源于对成都药市规模之大的惊叹。文献记载,成都“药市在大慈寺前”,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成都药市以玉局观为最盛”,可见,当年成都的药市,不仅规模大,而且不止一处,名声在外,直到元朝时仍然兴盛不衰。汪元量的此诗,虽然仅有“一道长街尽药香”一句算是对这处药市的具体描述,也足以让我们想象到当年成都药市的盛况。
其二是《蚕市》:
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
一岁蚕苗凡七出,寸丝那得做衣裳。
“成都美女白如霜”,劈头一句,真可算一部诗歌史上的神来之笔、穿越之作,如此的词汇,如此的句式,如此的俚俗,求诸今天的成都街头,简直和成都人的口头俗语毫无二致,读到这样的诗句,不能不让人既感到讶异,更感到亲切。

薛 涛
成都美女皮肤之白皙,历代闻名,源于四川盆地上空云层厚重,成都为其所庇,一年四季紫外线照射均不强烈。其实,汪元量的故乡吴越之地,女性的肤色也很洁白,杜甫就曾有“越女天下白”的诗句。汪元量来自吴越,本不该对女性之“白”如此少见多怪,但十多年前的1276年,汪元量就随南宋皇室移居北京,后来甚至移居内蒙古草原,蒙古地处高原,长年经受紫外线的照射,人们的肤色因此普遍较深。十多年来,汪元量习惯了女性较深的肤色,因此乍到成都时,看到遍街都是肤色白皙的美女,他不禁脱口而出,写下“成都美女白如霜”,让我们今天似乎还能看到诗人“眼前一亮”的神采,活灵活现。
美女们并不是千金小姐,她们是普通的劳动者,她们携着筐背着篓,成群结队,叽叽喳喳,有说有笑,要出城去采摘桑叶,完成她们一天的劳作。蚕市上出售各种与蚕业相关的物资和产品,如蚕种、蚕茧、生丝、竹筐、竹匾等,当然还有桑叶,每天市场上出售的桑叶,想必全靠这些青年女性到城外桑田里去采摘而来。
美女们貌若天仙,但身上的衣着却粗糙简陋,无非都是些麻葛织品。蚕农们一年忙到头,每年要收获七次,可尽管如此,美女们却没有哪怕一寸丝绸,用来为自己做一件漂亮的服装。汪元量对这些年轻女性充满了同情。
成都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古迹,汪元量在成都期间,不免都要一一游览。根据汪元量的诗,我们惊讶地发现,不少今天作为游览胜地的历史古迹,在当时早就是游览的热点,几百年来,并无变化。如:
草 堂
子美西来筑此堂,浣花春水共凄凉。
鸣鸠乳燕归何处,野草闲花护短墙。
英雄去矣柴门闭,邻里伤哉竹径荒。
安得山瓶盛乳酒,送分渔父濯沧浪。

成都最著名的历史遗迹是三国蜀汉政权的遗迹,汪元量在成都期间,也重点游览了这些遗迹,写下《锦江蜀先主庙》《后主庙》《丞相祠堂》等诗,如《锦江蜀先主庙》:
国破人何在,宫名喜尚存。
虽云蜀先主,犹是汉诸孙。
吴魏不相下,关张岂少恩。
崩年在三峡,遗恨满乾坤。
汪元量拜访三国遗迹,心情与一般游客有所不同,蜀汉的君臣是亡国之人,他自己也是亡国之人,所以在诗中,汪元量给予蜀汉君臣更多的同情。蜀后主刘禅国破投降,到北方后曾说出“此间乐,不思蜀”的名句,其情形与南宋幼主投降后到北方监视居住的遭遇很相似,这不能不引起汪元量的联想和共鸣。
某天,汪元量造访花蕊夫人的故居,留下了《花蕊夫人故宅二首》,其一:
千古风流一梦中,江山阅尽几英雄。
芙蓉城里家何在,花蕊夫人宅已空。
其二:
宅前宅后好青山,零落重门半掩关。
玉貌久归天上去,宫词百首落人间。
花蕊夫人是成都历史上的名人,是五代时期后蜀君主的后妃,据说貌美有才,创作有宫词百首,遗留人间。她的“故宅”在什么地方,今天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汪元量还能前去参观拜访,表明该处“故宅”,经过整个宋朝,直到元朝时尚存,并没有毁于宋元战争期间的战火。

花蕊夫人
某天,汪元量又登上成都的一段城墙,写下《蜀主芙蓉城》诗一首:
芙蓉城上草萋萋,吊古徘徊日欲西。
帝子不来花蕊去,荒唐无主乱鸦啼。
汪元量还拜访成都城郊著名的司马相如抚琴台,写下《琴台》一诗:
文园多病厌文君,恨入金徽不忍闻。
寂寞高台留古迹,来牛去马自成群。
汪元量游览的琴台,只是一个荒台而已,当时早已成为附近人家牧放牛马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今天的成都王建墓。王建是五代时期四川割据政权前蜀的皇帝,他的墓“永陵”在城西郭外。王建墓被误会为司马相如的抚琴台由来已久,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因人们在此开挖防空洞,才发现原来是王建墓。由此看来,王建墓被误会为抚琴台的历史,甚至有可能早在元朝。汪元量到成都的年代,距前蜀皇帝王建去世已有三百七十年之久,产生这样的误会,应该已有足够的时间。
因此,汪元量看到的琴台,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琴台,而是王建的陵墓,和花蕊夫人故宅、蜀主芙蓉城一样,都是五代时期的遗迹。
在成都期间,汪元量受到当地高官的很好接待,经常参加豪华的宴会,有一首以《锦城秋暮海棠》为题的长诗,就写到了这样一次聚会:
锦城海棠妙无比,秋光染出胭脂蕊。
日照殷红如血鲜,箭砂妆粒真珠子。
玉环着酒睡初觉,脸薄粉香泪如洗。
绛纱穿露水晶圆,笑杀荷花守红死。
蜀乡海棠根本别,有色有香成二美。
春花开残秋复花,簸弄东君权不已。
锦袍公子汗血驹,宾客喧哗间朱紫。
有酒如池肉如山,银烛千条照罗绮。
萧娘十八青丝发,手把金钟歌皓齿。
神仙艳骨世所无,歌声直入青云里。
江南倦客惨不乐,鸣笛哀筝乱人耳。
干戈满地行路难,屏里吴山数千里。
遥怜花国化青芜,浪蕊浮花敢欣喜。
草堂无诗花无德,窃号花仙宁不耻。
春花撩乱亦可怜,秋花烂熳何为尔。
花前妙舞曲未终,红雪纷纷落流水。
薄命佳人只土尘,抛杯拔剑长歌起。
此诗前十二句写“锦城海棠妙无比”。成都海棠花之美,四方闻名已久,在汪元量的笔下,海棠蕊如胭脂,殷红如血,粒粒如珠,美不胜赞,汪元量甚至用贵妃醉酒的形象来作比喻,甚至“笑杀荷花”“簸弄东君”,把成都的海棠,写得活泼俏丽、浓艳欲滴,到了极致。

上流社会的豪奢生活,在元朝的成都也毫无例外,公子、宝马、朱衣、紫袍、酒池、肉山、银烛、罗绮、美女、金钟、青丝、皓齿,“神仙艳骨世所无,歌声直入青云里”,诗句倾泻而出,写得生动传神,写得酣畅淋漓,当年成都城里的一次豪华盛宴,出于诗人笔下,如在读者眼前。可见作为一个诗人,文学史上留名的人物,汪元量写景状物的手段,也不输于任何一位比他更有名的诗人。
可是,“江南倦客惨不乐,鸣笛哀筝乱人耳”,面对眼前的富贵繁华,诗人的内心深处,更多的却是落寞的情怀和割不断的乡愁。“干戈满地行路难,屏里吴山数千里”,两句诗成为此篇的“诗眼”,点出了全诗的主题。看见屏风上面绘画的江南山水,诗人的思乡怀归之情油然而起,难以遏制。可是吴蜀两地,相隔万里,路途艰辛,何时才能回到家乡,见到屏中所绘的吴山?汪元量望眼欲穿,归心似箭。
在成都接待汪元量等人的主人是一位姓昝的官员,汪元量有多首诗提到此人的姓氏。宋元易代之际,四川有一个姓昝的有名官员,此人名叫昝万寿,南宋末年任“四川都统、知嘉州府”,曾在乐山等地组织军民抗元。1275年农历六月,昝万寿降元,被元世祖忽必烈赐名昝顺,后在成都任职,先后有“四川行省参政”“行诸蛮夷部宣慰司”等职务。显然,在成都接待汪元量等人的“昝相公”,就是此人。
昝相公席上
燕云远使栈云间,便遣郫筒助客欢。
闪闪白鱼来丙穴,绵绵紫鹤出巴山。
神仙缥缈艳金屋,城郭繁华号锦官。
万里桥西一回首,黑云遮断剑门关。
此诗第一句“燕云远使”的说法,显示了汪元量当时的身份,他是奉使而来,并非私人旅行,因此他得到成都官方的热情接待,理所应当。郫筒即用巨竹做成的竹筒,出自成都市郊郫县(今郫都区),用于盛装酒类,历史悠久。南宋范成大《吴船录》记云:“郫筒,截大竹,长二尺以下,留一节为底,刻其外为花纹。上有盖,以铁为提梁,或朱或黑,或不漆,大率挈酒竹筒耳。”
某次,昝氏还赠送汪元量锦被一段,不料却被汪元量婉拒了:
昝相公送锦被
蜀都府主迎宾客,赠我蜀锦三百尺。
美人蔌蔌弄金梭,鸳鸯机上初成匹。
繁花乱蕊皆同心,艳卉中含杜鹃血。
玉妃如霜姑射仙,金刀剪破云霞缬。
为我裁成合欢被,细意密缝无线迹。
道人把玩色相射,银海光摇泪珠滴。
却忆故家初破时,绣龙画雉如砂石。
绮窗窈窕花离离,红妆万境娇无力。
百幅锦帆风不动,绿湿红鲜荡春碧。
纷华过眼一梦如,蜀锦呈绫复何益。
白茅安用红锦包,虎皮难以裹羊质。
只今卷锦还府主,心地了然无得失。
铜壶漏断银缸灭,昆仑影转初三月。
道人坐久闻妙香,纸帐蒲团自清绝。

蜀锦工场
蜀锦是几百上千年前成都出产的著名产品,长年向朝廷进贡,天下闻名,人人艳羡。此次“蜀都府主”相赠的锦被,“鸳鸯机上初成匹”,刚刚由蜀女辛勤织成。锦被如此精美:“繁花乱蕊皆同心,艳卉中含杜鹃血”,这里的“杜鹃血”三字背后也暗指亡国。原来,史前时代的蜀王杜宇亡国后,曾化为杜鹃,绕成都周围飞翔鸣叫,不忍远别,天长日久,杜鹃随啼声呕出鲜血,染红了满山的杜鹃花。美丽的传说,隐含着凄凉的往事,汪元量暗引典故,写出了他面对如此精美的礼物,内心却泛起的一阵阵隐痛:想当年南宋朝廷投降之时,宫中的绫罗锦缎,其中显然就有由成都贡来的蜀锦,被弃如砂石,玉殒香消,“却忆故家初破时,绣龙画雉如砂石”。想到这些,汪元量“银海光摇泪珠滴”,他潸然泪下,“只今卷锦还府主,心地了然无得失”,最终他没有接受锦被的馈赠。
南宋末代皇帝赵显,年仅六岁就成了亡国之君,随南宋皇室成员北上以后,他被元朝封为瀛国公。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十三年后的1288年农历十月,元世祖忽必烈赐给瀛国公赵显宝钞百锭,命他赴西藏出家。关于此事,汪元量有诗述及:
瀛国公入西域为僧号木波讲师
木老西天去,袈裟说梵文。
生前从此别,去后不相闻。
忍听北方雁,愁看西域云。
永怀心未已,梁月白纷纷。
赵显赴西藏出家,途经四川入藏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直到今天,四川也是进入藏区的必经道路之一。也就在这一年前后,汪元量也来到成都,这显然不是巧合。
汪元量还有两首诗写于成都的远郊州县,其一是《蚕丛祠》:
西蜀风烟天一方,蚕丛古庙枕斜阳。
茫然开国人无主,仿佛鸿荒盘古王。
另一首为《青城山》:
敕使穿云破湿苔,水边坐石更行杯。
翩翩野鹤飞如舞,冉冉岩花笑不来。
乱木交柯盘圣井,数峰削玉并仙台。
平明绝顶穷幽讨,更上青城望一回。

此诗开头的“敕使”两字,点明了汪元量此行的身份,他确实身怀使命,并非来四川“自由行”无疑。西行途中,汪元量登上了青城山,由此深入丛山,经“松茂古道”攀援而上,就是进入藏区的必经之路。
当然,汪元量并没有将赵显送到目的地,他的诗集中未见有写于藏地的诗歌。他和赵显在某地分手了,“生前从此别,去后不相闻”,汪元量拜别旧主,掉头而东,回到杭州。十余年来的主仆二人,从此天涯悬隔,一在青藏高原,一在东海之滨,天高地远,生离已成死别。
以上就是诗人汪元量在成都的故事。不要忘了,如果我们推测不错的话,在成都的汪元量身边,始终还有一个要紧的人,他就是南宋的末代皇帝、大元朝的瀛国公赵显。谁说元朝的成都没有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的更多细节,我们今天还不了解而已。
汪元量的诗也向后人证明,即便在元朝,成都仍然是一个繁荣、安乐的城市。
(载《巴蜀史志》2019年第1期,总第221期)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